富士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 > 第26章 烧不掉的纸(第1页)
第26章 烧不掉的纸(第1页)
沈玉梅的能量果然不小,不过两天,苏霓就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见到了那位返聘的清洁工王阿婆。
老人头花白,身形佝偻,一双布满皱纹的手局促地在洗得白的围裙上反复擦拭。
岁月和生活的重压在她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烙印,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怯懦与不安。
“沈主任都跟我说了……”王阿婆的声音又轻又颤,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姑娘,你要问八年前的事?”
苏霓没有急着开口,而是先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一股温热的姜茶香气瞬间弥漫在狭小局促的客厅里。
“阿婆,外面天冷,您先暖暖身子。”她将杯子递过去,目光温和而真诚,“我不是来审问您,只是想知道一些真相。有些人的清白,不能被埋没一辈子。”
“清白……”王阿pei重复着这两个字,浑浊的眼眶瞬间红了。
那温暖的杯壁仿佛传递了某种力量,她颤抖的手终于稳了些。
沉默良久,她像是下定了天大的决心,转身走进里屋,在一个上了锁的旧木柜里,吃力地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饼干盒。
盒子打开的瞬间,一股陈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没有金银,只有几张已经泛黄的照片和一沓用塑料袋精心包裹的复印件。
“出事那天,是我当班,我亲眼看见,是周主任带人搭的架子,用的卡扣根本不对!我跟工班长提了一句,他还骂我一个扫地的懂什么。”王阿婆指着其中一张照片,照片上,舞台一角的结构清晰可见。
“后来塌了,他们第一时间就来找我,让我闭嘴,说这事跟我没关系,台里会处理。然后,就给了我三个月的奖金……”
老人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了八年的委屈和愤怒,“可我知道,不是我的错!他们说我打扫的时候碰倒了关键的支撑,纯属胡说八道!”
苏霓的目光落在那些复印件上。
其中一页,赫然是当年的内部处理通报,白纸黑字写着:“经初步调查,事故系临时工王某操作失误所致,责任归于个人。”
而在这行字的末尾,那个龙飞凤舞、她再熟悉不过的签名,如同一根毒刺,狠狠扎进她的眼里——赵德海!
竟然是他亲笔批示!
苏霓的心脏猛地一沉,一股寒意从脊背窜上头顶。
原来从八年前开始,这张巨大的网就已经铺开,赵德海就是那个稳坐蛛网中心的毒蜘蛛!
她小心翼翼地将所有资料收好,郑重地对王阿婆说:“阿婆,谢谢您。请相信我,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离开王阿婆家,苏霓没有片刻耽搁,立刻驱车来到陆承安的律所。
当陆承安看到铁盒里的一切,尤其是赵德海的亲笔批示时,他深邃的眼眸中也闪过一丝凛然。
“这还构不成直接证据,年代久远,对方完全可以辩称是初步意见,后续已有纠正。”陆承安冷静地分析,“但你说的没错,它是一枚完美的导火索。”
夜色渐深,律所的灯光却亮如白昼。
陆承安连夜整理材料,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敲击,将一份匿名举报信的框架搭建起来。
“听着,苏霓,”他将一份草稿推到她面前,“你以‘关心电视台展的热心观众’名义,将这张批示复印件、照片,以及王阿婆的部分证词,打包寄给纪委驻台监察组。”
苏霓看着信的末尾,陆承安特意加了一句点睛之笔:“若今日之‘秩序’,是建立在昨日之冤屈上,那么这样的秩序,是否也该被重新审视?”
“光有这个还不够,”陆承安继续说道,“你需要一个引子,在公开场合释放一个信号,逼他们自乱阵脚。人一旦心虚,就一定会做出多余的动作来掩盖。”
几天后的台务会上,气氛一如既往的严肃。
副台长黄志远提出了一个关于增设“青年创新基金”,用以扶持台内青年独立制作团队的议案。
话音刚落,赵德海便沉着脸第一个表示反对:“我不同意。年轻人思想活跃是好事,但经验不足,做事毛躁,缺乏大局观。电视台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拿来给他们试错。万一出了事,谁来负责?”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不少人都暗自点头,觉得赵德(德)海说得在理。
就在这时,一声极轻的笑声打破了沉闷。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苏霓身上。
她仿佛没注意到众人的视线,只是慢悠悠地转着手中的笔,嘴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赵台说的‘出事’,我倒是深有感触。我记得大概八年前,台里也出过一次不小的舞台坍塌事故。”
“嗡”的一声,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
赵德海的脸色瞬间僵住,握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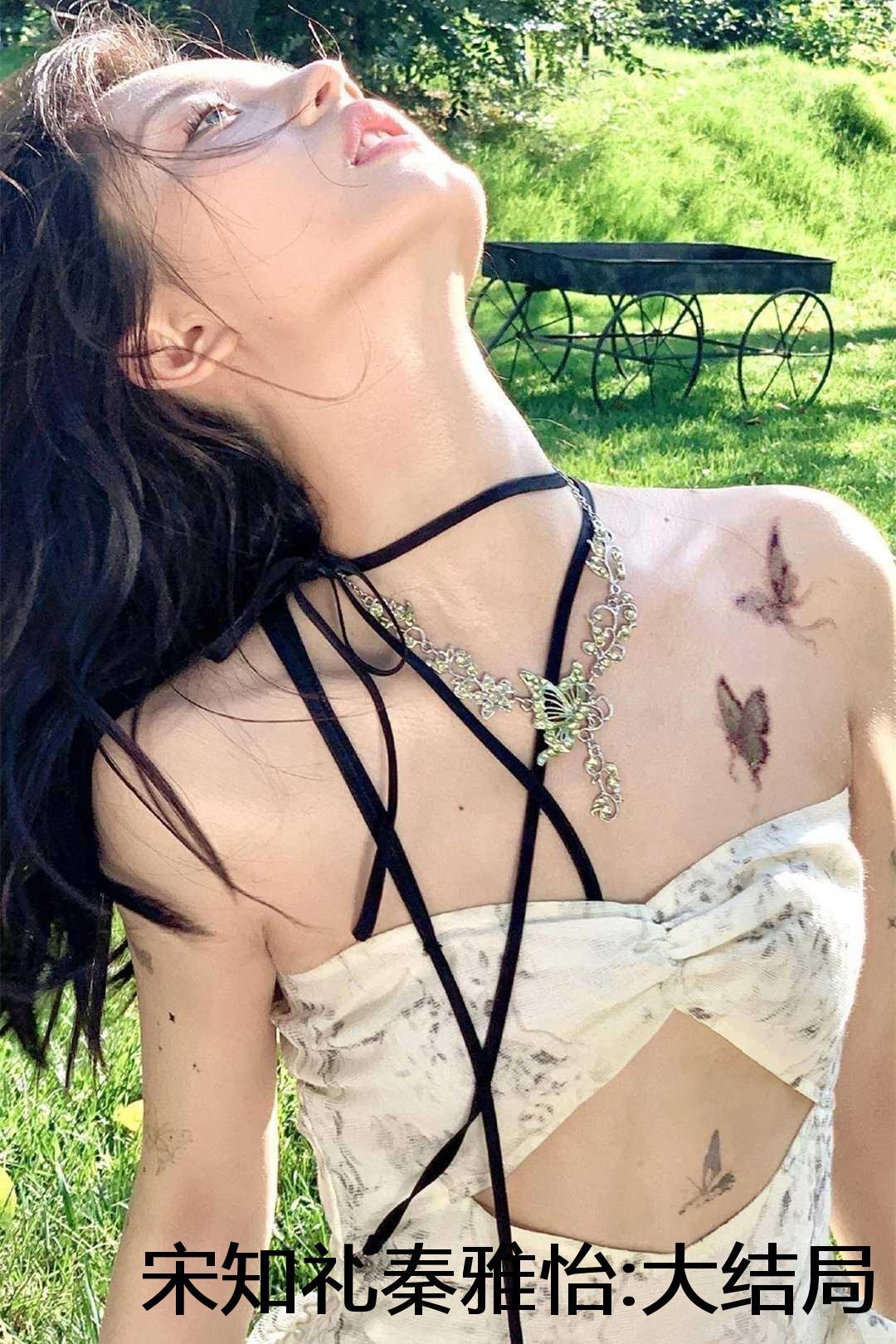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