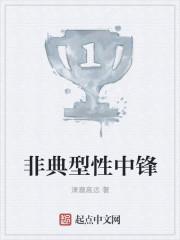富士小说>八零后女神 > 第338章 没人拿话筒那天才算成了(第1页)
第338章 没人拿话筒那天才算成了(第1页)
但这一次,信号的稳定并未带来任何改变。
江畔那个名为“声音接力角”的话筒,依然死气沉沉。
春寒料峭,低温成了最完美的借口,连续三天,它拒绝接收任何人的心声。
技术部门的报修单雪片般飞向林晚的案头,催促的电话几乎要将她的听筒融化。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城市的倾听之耳坏了,必须立刻修复。
“再等等。”林晚的命令简洁而又不容置疑,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一片困惑的涟漪。
她挂断电话,推开所有文件,穿上最不起眼的外套,走进了江畔的冬雾里。
她不是去检查那个故障的话筒,而是去寻找那些被话筒拒之门外的声音。
她的预感是正确的。
声音,如同被堵住的河流,总会找到新的河道。
在一个老旧小区的楼道里,她隔着门板,听到一位老奶奶正对着一台老式录音机,絮絮叨叨地讲述着今天市场的菜价,末了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这是给江边那个话筒的,等它好了,我让我孙子帮忙传上去。”林晚在笔记本上记下:自代偿录音,一号。
很快,她找到了二号和三号。
一位是深夜加班的程序员,用手机备忘录录下对代码的咆哮和对未来的迷茫;另一位是失恋的女孩,在被窝里用k歌软件清唱着不成调的悲伤,她把每一段都命名为“江边回响”。
最让林晚震撼的,是在话筒旁的栏杆上。
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因为没有录音设备,竟用作业本一笔一画地抄写着自己想说的话,字迹稚嫩却用力。
那是一篇关于梦想的作文,结尾处写着:“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话筒,因为它从来不笑话我。”孩子把作业本撕下来,用红色的绳绑在冰冷的金属栏杆上,像系上一个无声的祈愿符。
第四天清晨,天还未亮透。
一群背着双肩包的少年,带着满身的朝气冲破了薄雾。
他们没有去摇晃那个失灵的话筒,而是熟练地架起了一台便携式蓝牙音箱和一支手持麦克风。
一个看起来像领头的男孩,小心翼翼地解下那张写满字的作业本,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介于少年清亮和成年低沉之间的嗓音,对着“土法扩音器”朗读起来。
“我想……我想告诉话筒,我的梦想是……”
寒风中,那稚嫩的文字通过简陋的设备,在江畔回荡。
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少年走上前,轮流朗读着那些被贴在栏杆上的、写在零食包装纸背后的、画在便签条上的“留言”。
他们成了临时的信使,成了那些沉默声音的扩音器。
林晚藏身在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后,举着手机,冰冷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她录下了全程,从第一缕晨光照在少年们年轻的脸庞上,到最后一句“我的话说完了”消散在风里。
她低下头,在视频文件的命名框里,郑重地输入了六个字:《没有麦克风的主持》。
这段视频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当晚就被上传到了“声音接力角”的官方主页。
它像一颗投入深海的炸弹,瞬间引爆了整个网络。
苏霓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看到这段视频的。
落地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室内只有一盏台灯散着暖光。
她没有像普通网友那样被少年们的热血所感染,她的目光,死死锁定在其中一个男孩的脸上。
那男孩手里拿的不是纸条,而是一本翻开的语文课本,他对着麦克风大声朗读着自己刚写的作文:“老师说,我们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有意义。可是我觉得,能有机会把它说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一句话,仿佛一把钥匙,精准地插进了苏霓尘封多年的记忆锁孔。
她没有转,也没有点评,只是缓缓起身,走到书房最深处的保险柜前。
她取出了一盘早已停产的betaca录像带,那是她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站上电视台演播室的珍贵记录,是她职业生涯的,也是她荣耀的徽章。
她凝视着录像带,仿佛在看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良久,她拔下钢笔的笔帽,在录像带末尾那段仅有的几分钟空白处,一笔一划地写下一行字:“这一分钟不属于我,属于所有没说完的人。”
第二天,她亲自将这盒被无数人视为“主持界圣物”的磁带,捐赠给了本地传媒学院的影像资料馆。
在交接单的备注栏里,经手人犹豫着问她该写些什么,是“传奇的见证”还是“荣耀的开端”?
苏霓只是淡淡一笑,拿起笔,只填了一句:“请让它坏在学生手里。”
与此同时,远在数据中心顶层的许文澜,也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暴的另一个侧面。
后台数据显示,“代偿录音”正在以惊人的度演变成一种新的网络行为艺术。
无数用户开始在上传自己的录音时,刻意模仿那个故障话筒的声音质感——他们主动加入电流的杂音、断断续续的卡顿,甚至模拟低频的嗡鸣。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们在标题里标注:“这样更像真的在江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