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陷入恋爱的内心与魔法的言语 > 第67章(第1页)
第67章(第1页)
因为高热而声困难的嗓音还未恢复,于是他叫星野佑靠的近些,直到那颗晃着浓密金的脑袋充盈视野,费奥多尔才出了口气。
他压低声音,端住一分两分的委屈和茫然才问:“yuu是不是生气了?因为我……”
星野佑呆住,转过头来正面盯着费奥多尔,浓绿的眼睛闪过的茫然只比费奥多尔更多。
他来不及等费奥多尔的呈堂词供,便迫不及待的打断了对方的诘问:“没有——完全没有,费佳是我要好的、说是最好的朋友也不为过的。”
星野佑觉得冤枉:“费佳为什么会这样想?”
费奥多尔眯了眯眼,在病人身上的威慑力理应无限趋近于零,偏偏星野佑却觉出了两分危险的意思。
“大概就是因为昨晚在计程车上您的那个问题。”
费奥多尔像是找到了仰仗,即便是躺在了病床上气势也以压倒性的优势逼退了星野佑。
“您为什么会为了那个问题而感到不高兴呢?”
费奥多尔的眼中是真实的疑惑:“【星野佑】与【伊恩】两个名字于您有着不同的意义?”
他微微叹气,像是在为什么而感到遗憾:“抱歉,我对您的心事并不知悉——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哄您开心的机会。”
俄语在通常的讲述中是有些凌厉囫囵的,但或许是因为有些虚弱,又或许……是因为费奥多尔讲这话是格外温柔,星野佑觉着自己的耳尖被烫了一下,随即悄悄的烧了起来。
他抿紧唇瓣,目光紧紧的盯着自己的友人,对方也坦然的望过来,任由星野佑打量,最后依旧是星野佑率先败下阵来,撇开头闷闷的说不是你的错。
他深呼吸:“这两个名字都很好,你的回答也没有问题,是我自己有问题。”
费奥多尔蹙眉,并不像是信了的样子。
“真的。”
星野佑呼出口气定了定心神,又重新和他对上目光:“费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只是……有些不满足。”
“不满足?”
费奥多尔有些困惑,他似乎总是被星野佑奇妙的想法而产生这样原本陌生的情绪。
“费佳是我最好的朋友。”星野佑再一次强调重复道:“但在我问起你那个问题时,你的反应是不希望惹我生气——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回避。”
“或者拒绝。”
话音落下,单人病房中归于静谧,星野佑心虚的将目光转向天花板,完全没有注意到费奥多尔在那句话后怔愣的眼神。
原来,原来。
原来只是这样。
费奥多尔觉得有些好笑,因一人的情绪而感到烦躁对他而言曾是天方夜谭,不求回报的计划只因对方的期待——他似乎星野佑的情绪而做出了许多于他而言并不值得的事情,尽管他在做时乐此不疲。
初衷是什么?哦,因为星野佑的背后——他背后的马普尔女士,再由马普尔女士而延伸出的斯特拉福先生,再到乔安妮……
星野佑并未对他有所隐瞒,他们之间的交际符合正常的规范,他也做到了一个朋友理应去做的事情。
但似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比起他身后的一切,更加牵动死屋之鼠头领心神的,成为了这个人本身。
或许是在伦敦的机场巴士上的宽慰,言辞在寻常的社交辞令中有些过火;或许是在演奏会的承诺后,主动要求再送一束花本身便不合情理。
又或许是在最初的最初,在那间捷里别尔卡的木屋里,那个堆着积雪的帐篷里,他们乘着临时找来的船只去追鲸,在燥热的客厅里演奏糖果仙子之舞。
那些其实都没什么意义,第一次递给他卡林巴拇指琴时也是不动声色的拒绝,可偏偏还是同意了,因为那人期待的目光不应落空。
从友人这一定义来权衡他对星野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有些过火。
而现在,他的目光聚焦在尴尬分神的星野佑身上,他正在在为自己的任性想法而不敢看过来,费奥多尔又觉得好笑。
他们似乎都没有现现在的关系似乎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畸变——至少不算健康,但费奥多尔无意做出改变,与之相反,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切合的词语来定义这份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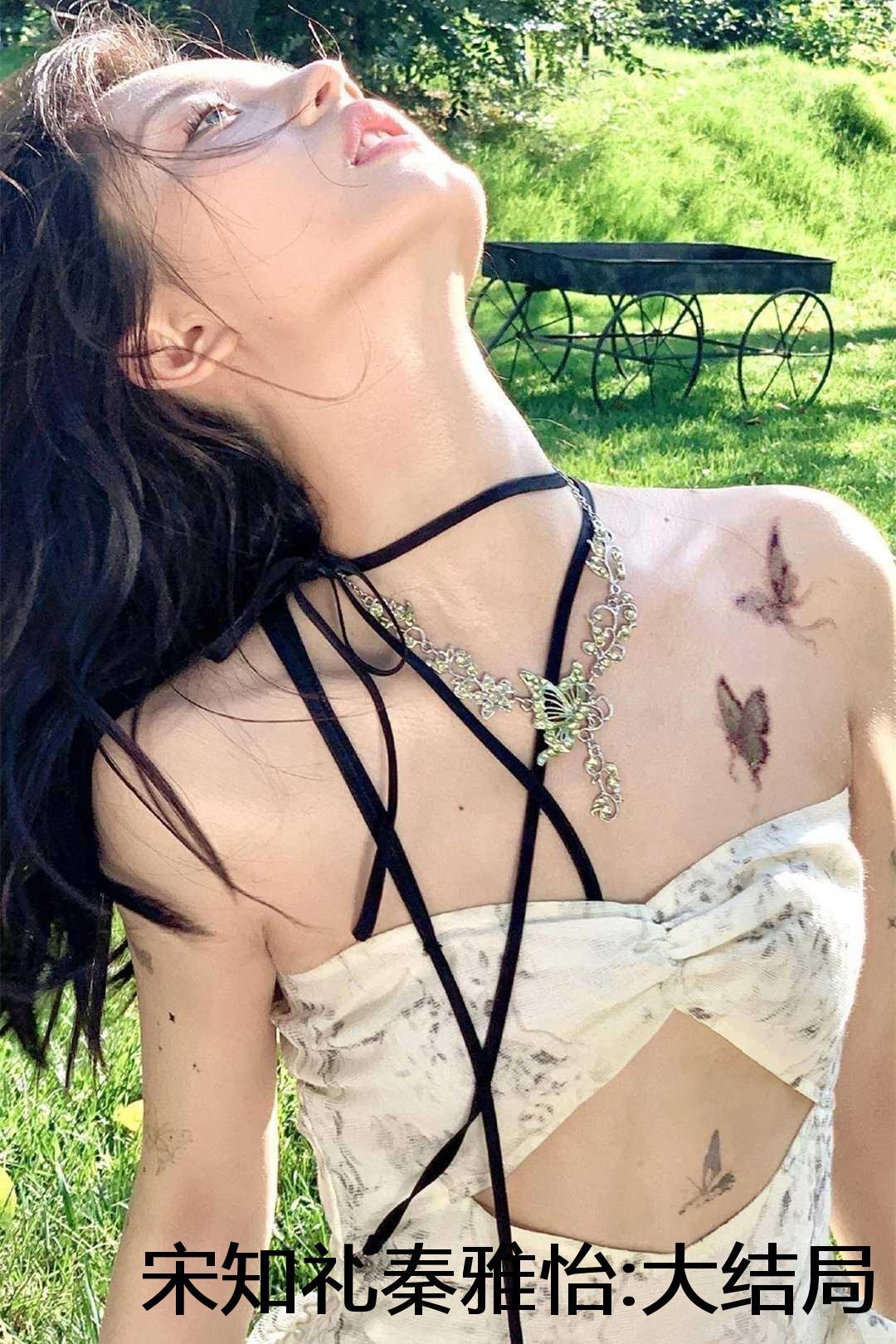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