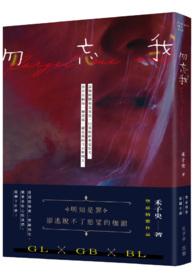富士小说>橙光游戏三国金手指破解版 > 第312章(第2页)
第312章(第2页)
她人虽已不在睢阳,但她留下的烙印,如同烈火灼过草原,即便春风吹又生,即使标簽从中作梗,那深刻的痕迹也断然无法抹去。
可是,席间,一个声音怯怯地响起,大司马草菅人命,杀伐太重
你懂个屁!王越闻言勃然大怒,激动地拍桌而起,那叫杀伐果断!乱世用重典,否则何以立军?何以平乱?若是人人都优柔寡断,天下何时能定?
说话那人被他吼得面红耳赤,噤若寒蝉,不敢再言。
众人纷纷点头,气氛一时热烈起来。
他们怀念的,正是谢乔身上那股不容置疑的权威,那种以结果为导向、摧枯拉朽的执行力。
在太师的文治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正确,那么温和,却也那么缓慢。
一项政令的推行,需要经过满朝文武的反复商议,需要引经据典,需要照顾各方情绪。
对于他们这些习惯了雷厉风行、渴望建功立业的实干派而言,这种温吞的节奏无疑是一种煎熬。
在下听闻,大司马被逐出睢阳后,并未消沉,回了老家凉州兴兵,重整旗鼓。有人压低声音说。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当真?
陇西苦寒,羌人环伺,大司马竟能如此迅站稳脚跟?张武不敢置信地问道,他深知边郡的艰难。
我早就说过,大司马乃人中龙凤,岂会甘于沉寂泥沼之中!
李谦听着众人的议论,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重重放下:若非家有八旬老母需要奉养,我真想立刻投奔凉州,再为大司马执鞭坠镫,效犬马之劳!
没错!与其在此蹉跎岁月,不如去西凉追随大司马,开疆拓土!
大丈夫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
我也有此意!可惜边塞路远,匪患猖獗,我等皆是拖家带口之人,万一路上出了差池,岂不是连累家人?
众人都沉默了,眼中满是无奈,激情被冰冷的现实浇熄。
他们心向谢乔,却也被家庭、责任、名声和现实的安稳牢牢地束缚在睢阳。
朝堂之上,圣人太师谢均的威望如日中天,他仁德宽厚,礼贤下士,已经成为天下士人心中新的标杆。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表达对一个被贬斥的大司马的怀念与追随,无异于政治自杀,会被立刻打上不忠的标簽。
但私下里,这种情绪却在故吏心中酵,寻找着爆的出口。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场小小的聚会,从第一句叹息开始,就已经被一张无形的大网捕捉。
数日后,李谦、王越、张武等十余名参加过那次宴饮的官吏,都在同一时间,接到了来自太师府的秘密传召。
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夜色的掩护下,从不同的路径,被引入了太师府一间戒备森严的密室。
密室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长案和数排坐席。
当谢均一袭便服,面带微笑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所有人心头一紧。
王越甚至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死则死矣,以死明志,在所不惜!
诸位不必紧张,请坐。谢均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和,仿佛只是邀请友人夜谈。
众人依言坐下,却如坐针毡。
谢均没有兜圈子,开门见山地说道:诸位近日的忧思,以及那夜的感慨,我都已知晓。
一言既出,满室死寂。
李谦等人脸色煞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王越猛地站起,昂挺胸,直视着谢均道:太师!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等心怀旧主,与旁人无干!我等感念大司马知遇之恩,此心不改!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他喊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众人纷纷挺直了腰杆,准备一同赴死。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谢均没有动怒,脸上的微笑甚至没有丝毫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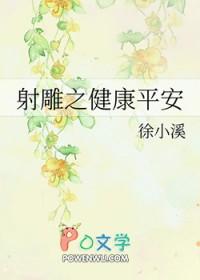
![女配她刀长四十米[七零]](/img/2069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