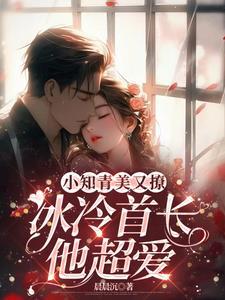富士小说>庶女攻略病弱皇子的千层套路漫画 > 第92章 投票那晚没人睡(第1页)
第92章 投票那晚没人睡(第1页)
昌平拾遗亭外,三丈高榜在风中猎猎作响。
黄麻纸上墨迹清晰,苏婉儿的忏悔书全文与芸娘生平摘要并列张贴,字字如刀,刻进每一个驻足者的视线里。
榜下设一漆木投票箱,左右两侧分别凿着“录”与“不录”二字,箱口窄得只能容一手伸入,杜绝舞弊。
规则写得明白:凡年满十二者皆可投一票,不限身份,不论出身。
天刚蒙蒙亮,队伍已蜿蜒出半条街。
来的多是穿着粗布衣裳的女子,有挽着髻的仆妇,也有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庶女。
她们沉默地排队,目光却灼热。
有人攥着票纸反复摩挲,仿佛那不是一张轻飘飘的纸,而是多年压在胸口的一口气。
赵砚之的人果然来了。
他们在巷口散播流言:“投‘录’者,便是认贼作姐,往后在族中抬不起头。”这话原是冲着动摇人心去的,可没过两日,街头巷尾竟传出另一股声音——
《一个婢女的女儿能走多远》。
韩霁主笔,报馆连载,每日一更。
讲的是芸娘同村一位女孩,靠拾遗助学金读女塾、考文试,如今已在工部任文书助理。
文章没有煽情,只用事实说话:她识了字,写了第一封家书;她挣了月俸,给母亲买了药;她站在衙门前,没人敢再唤她“丫头”。
百姓不傻。他们看得懂谁在造谣,谁在照亮。
舆论悄然逆转。
那些曾犹豫是否该“宽恕”的人,开始问另一个问题:我们记录过去,真是为了清算吗?
还是为了让下一个芸娘,不必再死?
萧澈在府中听柳知秋汇报民情时,正倚在窗边喝茶。
他病体未愈,脸色泛青,眼神却清明如刃。
“礼部昨夜授意京兆尹,要限拾遗亭夜间开放。”柳知秋语气微紧,“说防‘聚众滋事’。”
萧澈轻笑一声,将茶盏放下。
“防?他们怕的不是滋事,是光。”他缓缓起身,披上外袍,“既然怕黑,我们就点灯。”
当夜,国子监贴出告示:起“守夜共读会”。
每晚十名太学生轮值,为不识字者朗读候选材料,代录口头意见。
消息传开,应者云集。
第一夜,雪落无声。
拾遗亭内烛火通明。
一名盲眼老妪拄杖而来,白被风吹乱。
她坐在角落,听学生一字一句念完芸娘遗言录音稿——那是苏锦黎命人从旧档中复原的语音残片,经技术还原后仅存三十七字:“我想读书……娘,我不要被卖掉……”
老人浑身颤抖,枯手抚过投票箱边缘。
“我闺女也是这么没的。”她喃喃道,“她才十岁,就被牙婆拖走,再没回来。”
她举起手,声音沙哑却坚定:“我投‘录’。”
在场众人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