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庶女攻略皇后 > 第81章 他们不是在等赦令是在写新律(第1页)
第81章 他们不是在等赦令是在写新律(第1页)
清明刚过,京城的风里还裹着纸灰的气息。
韩霁站在太学门前,手中捧着一叠墨迹未干的奏稿,指节白。
内阁驳回《拾遗保护法》那天,他没有争辩,只问了一句:“若祖宗之法不可变,那百姓的记忆,算不算新法之基?”
无人作答。
三日后,太学门口搭起一座木台,四角悬陶铃,中央立一块空白石碑。
韩霁亲自执笔写下四个大字:万民立法。
他不讲经,不传道,只设一张案、一摞纸、一支笔,请过往百姓口述他们心中的“该与不该”。
第一日,来了卖菜的老妪,说:“官仓放粮要有人盯着,别再拿霉米当恩典。”
第二日,书童模样的少年蹲在台边,低声念:“孩子走失,里正得报官,不能说是‘自己跑丢的’。”
第三日清晨,柳知秋带来一封岭南来信,纸上歪斜写着一行童言——
“大人说谎要刻陶片挂墙上。”
韩霁盯着那句话看了许久,忽然笑出声,眼底却泛红。
他命人将这句抄在最显眼处,又从灰屋纪念馆调来当年“灯变案”的陶片证据,按时间、地点、人物分类,附于每一条民间建议之后。
两千三百七十六条,最终被整理为七章五十四条。
奏本题名《民之所欲,法之所向》,送入宫中。
皇帝阅至深夜。
烛火跳动间,他的目光停在那句孩童所言上,久久不动。
次日早朝,内侍捧出朱批原稿,全场屏息。
皇帝只写了五个字:
“此非臣奏,乃天问。”
殿上寂静如渊。
就在这时,萧澈自列班中缓步而出。
素日病弱的模样不见踪影,步伐沉稳,声音清冽如寒泉击石。
“陛下既闻天问,不如顺天而行。”他取出一份新策,“臣请设‘双轨修律制’:凡新法颁布前,必经两道查验——其一,由独立修史院核其是否违背贞元教训;其二,交拾遗亭网络,征询民间反馈。”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礼部尚书:“试之法,便是《赈灾稽查令》。”
随即展开条文:“禁止以琉璃泡充赈品。”
满殿哗然。
礼部尚书当即出列:“岂能因一事立一法?荒唐!”
“是啊。”萧澈轻轻接话,眼神却不怒,“若十年前有此法,江南水患那三千石粮米,会不会多活三百人?”
无人回应。
唯有檐下铜铃轻响,像是替亡魂叹息。
数日后,刑部悄然挂牌“历史合规司”,主官正是沈砚舟。
他并未大张旗鼓,只命书记官将“灯变案”中贵族借赎金逃责的陶片证据制成展板,陈列于大堂正中。
来办事的百姓抬头便见:某郡公之子流徙三千里,赎银八千两,当日到账;而邻县九品小吏同罪,无力缴纳,死于押解途中。
对比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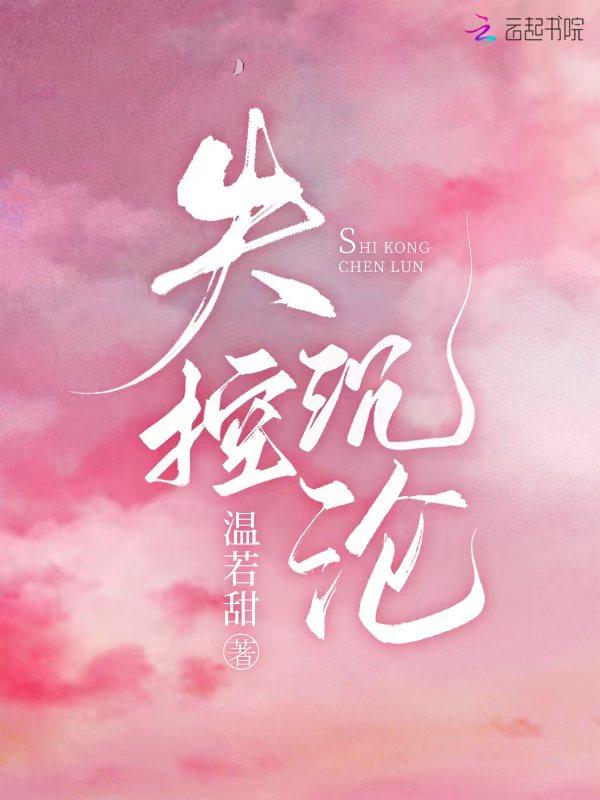

![心动对象全是皇子马甲[gb]+番外](/img/272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