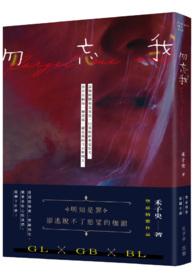富士小说>北雪融冬笔趣阁 > 第46章 重逢(第2页)
第46章 重逢(第2页)
沐川敛去杀意。
舞女坐在身侧,规规矩矩倒酒。
潘仪声音尖细,“若老曹没抢殷红,高远王也不会跑到西陲荒凉地。”
唐志远摆摆手,睁眼说瞎话,“本王对丞相没任何不满,去西陲就是为了散心。”
曹明诚举杯,哈哈笑道:“高远王深明大义。”
说给唐志远的话都是为了敲打他,暗指:不要不识擡举。
曹明诚见沐川没有举杯的意思,绕了大半圈终于切到正题,“东川侯闷声不吭干大事,有皇帝做靠山,怪不得对我们冷眼相向。”
潘仪阴阳怪气道:“皇帝能让左平安消失,我们也能让班飞光消失,朝廷的人消失也不是个事儿,不若化干戈为玉帛。”
之前总想着自己不够强大,遇到冷嘲热讽总觉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傅初雪让他意识到,正是因为自己的忍让,才让奸佞更加猖獗。
得罪人不可怕,窝囊的活着才可怕,若不奋力一搏,永远都不能变得强大。
三方会审被压制,此番决不能再当鸵鸟。
沐川说:“听闻丞相儿子前几日与户部侍郎儿子在司礼监起争执,户部侍郎与其理论,丞相儿子说‘我父亲是朝中最大的官’。”
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暗指他知晓曹明诚儿子的一举一动,以此要挟;二是他们设宴,就说明对皇帝有所忌惮,曹明诚儿子说了不该说的话,沐川用皇帝施压。
此前空有一腔孤勇,说话直来直去,受傅初雪侵染,逐渐学会了与奸佞沟通的正确方式。
沐川的行事作风,思考方式都在下意识模仿傅初雪,就像他一直在身边。
此话一出,曹明诚神色骤变。
潘仪打圆场,“东川侯向来寡言,今日说话怎麽夹枪带棒?”
沐川淡淡道:“丞相无需在意,女儿不是您的,儿子也不一定是您的。”
殷红打翻杯盏,唐志远瞪大双眼。
曹明诚:“你……”
他只不过将他们不要脸的行径摆到明面上说,他们却敢做不敢认。
“东川侯南征北战,功高盖主,说话直白猖狂些,咱家都能理解。”潘仪说,“今日我等相聚于此,就是想和气生财,做人留一线日後好相见。”
潘仪平日在诏乐殿伺候,说他功高盖主,就是想离间他和皇帝。
面上细数他的功德,背地里将刀磨了好几遍。
万万没想到全场最稳当的竟然是潘仪。
沐川起身,缓缓走近,俯身嗅了嗅,淡淡道:“先帝赐你的香再香,也盖不住尿骚味。”
“哐当”
潘仪腕间祖母绿手镯狠狠砸向案几。
丝竹声未停,但琴师的指法似乎乱了半拍,双方彻底撕破脸。
曹明诚直言不讳道:“龙封坡之事,皇帝压了五年,就能再压五年,你在内阁没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沐川眸色微闪。
潘仪又开始唱白脸,“东川侯在西陲审死知县知州,名动朝野,可此等行径无异于说皇帝用人不贤。若东川侯执意追查通倭,搅得朝堂天翻地覆,到时龙颜震怒可就不好了。”
说不动便搬出皇帝压人。
沐川自知逆鳞不可触碰,可十万忠魂死不瞑目,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为了复仇断情舍爱,怎麽能轻易地妥协?
阴沉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个人,最後落在潘仪身上,沐川慢条斯理地开口,“我本不想来,此番是卖高远王面子。”
曹明诚:“来人!”
“在!”
锦衣卫鱼贯而入。
沐川摔了杯盏,亮出禁军兵符,左右卫冲入安寿楼。
上次入宫,皇帝便将兵符交与他,说:“大虞皇宫禁军十二卫,全凭将军调遣。”
两军对峙,楼中空气凝滞,落针可闻。
这场盛宴自始至终,未敢放松片刻,当沐川走出安寿楼,夜风一吹,才发觉自己的後背竟在不知不觉中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夜幕沉沉,唐志远小跑跟在身後,行至远处,沐川说:“刚我尽力了,他们……”
唐志远摆摆手,说:“他们屡次用曹雪要挟,之前本王总想着‘这最後一次任人摆布’,今日之事让本王看清,不可与蛇鼠共谋。”
沐川问:“你想告诉我傅初雪的什麽事?”
唐志远刚要说话,不远处驶来一辆马车,夜间看不真切,车夫的身段有几分眼熟。
车帘缓缓掀开,沐川望过去,便再移不开眼。
擦肩而过时,焦宝故意放慢车速,猛使眼色。
唐志远只见刚刚给对朝丞相丶掌印太监冷言相向的东川侯似中了邪术,屁颠屁颠地追着马车跑,边跑边叫:“祈安,祈安,祈安……”

![女配她刀长四十米[七零]](/img/2069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