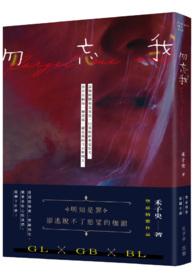富士小说>皇上傀儡禅让 > 第九十七章(第2页)
第九十七章(第2页)
进来的侍卫是禁卫军,虽然负责保护王氏的安全,但他们却不受命王氏。
最重要的文初是帝王,皇宫中邢宵统领的禁卫军只听凭谢怀枭的话,其馀人无论是谁,一概不会听凭。
文初心中都是要为玉儿报仇,此刻手握着长剑,便向王氏和白容二人刺了过去。
文初已经猜到,玉儿受害,不只是白容一个人,王氏定然脱不了干系,两人是狼狈为奸。
侍卫见文初挥剑冲着王氏去了,忙上前去阻止,宴商舟横在禁卫军们面前,与他们打了起来。
谢怀枭也早便来了,只是气郁王氏,显然谢怀枭也想到虐打玉儿一事不是白容一人所为,他没有那个胆子。
人颦着眉,盯着文初,只是他没想到,文初手握长剑,居然去向王氏刺去,这个幕後指使者,而不是行凶的人白容。
再气,也是生养教导他的母亲,恩情重于泰山,谢怀枭指尖上捏的石子一弹。
一道破空响,下一刻“啪嗒”一声,文初手中握的长剑落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嗡鸣。
白皙的手腕被尖锐的石子破开一道口子,紧接着有鲜血流了下来。
王氏已经被文初惊的脸色煞白,显然也没预料到,文初居然毫无不迟疑的刺向她。
白容伤了他的孩子,她又是谢怀枭的母亲,他却丝毫没有顾虑要杀她。
王氏忙避开文初,向着门口出现的谢怀枭奔去。
虽然王氏清楚谢怀枭会保护着她,但刚受到惊吓的她,还是觉得守在谢怀枭身旁最为安全。
文初手腕上滴答着殷红的鲜血,可却不见他有疼痛的样子。
右手受伤了,他便用左手丝毫不耽误时间的捡起地上的长剑,向着白容刺了过去。
白容也看到了谢怀枭:“怀枭,救我。”
殿内动静这麽大,却不见有其他侍卫进来,明显是因为站在门口的谢怀枭。
今日为了玉儿,他是要让白容得到应有的惩罚。
白容虽然极力躲避着文初,但他身体也不好,一个不留神就被文初一剑刺在了肩膀上,白色的衣料瞬间被鲜血染红。
文初是想杀了白容,一剑不中,又刺去了第二剑。
白容一直呼喊着谢怀枭救他,谢怀枭却一直冷漠的站在原地。
王氏从惊吓中缓过来後,与谢怀枭道:“他到底是你的王妃,你就看着他被那个文家小儿杀了吗?”
又提醒他道:“当初在猎场可是白容不顾及生命危险,为你挡下了致命的一剑,尤其他是听凭我指使而为之的。”
王氏很清楚这件事,她是无法将自己摘干净的了,不如坦然承认。
自从她杀了勒而兰後,没有後顾之忧,她可以毫无顾虑的顶着这个孩子亲生母亲的名头,随意的教育他,哪怕是她的错。
“母亲,”谢怀枭满心无奈的道:“儿臣已经说过多少次了,玉儿的事,你不要插手了。”
“怀枭啊,”王氏语重心长的道:“你喜欢孩子,可以让白容为你生啊,那个玉儿,是文家的孩子,身体里流淌的是文家的血,是你的仇人啊!”
谢怀枭第一次感觉到了心累:“母亲,总之玉儿不可有事了。”
王氏忽然静了下来,仔细端详他一刻後,道:“莫非玉儿是你的骨肉?”
“母亲,”谢怀枭道:“现下大周国最不应该发生意外的人就是玉儿,龙蜀国蜀帝怕是就等着玉儿有事,他好,唉,这事情说来话长,以後儿臣再同你解释。”
白容已经被文初刺了两剑,眼瞅着已经没有力气再躲避了。
谢怀枭闪速过去,一把攥着文初持剑的手腕,指尖一捏,下一刻文初的手腕脱臼,唇瓣溢出一声痛吟,脸色被痛的惨白,怒视着谢怀枭。
谢怀枭不看文初,将文初推给奔过来的宴商舟。
文初被疼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尤其玉儿病危之事对他的打击太大。
体力也经这一番耗尽,人躺在宴商舟怀中,晕死了过去。
宴商舟忙将人抱走去,处理伤口和脱臼的手腕。
白容脸色赤白,忍着身上伤口的疼痛,跪在了谢怀枭面前,眼中泪水横流,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的对谢怀枭说道:“怀枭,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这种情况下,他无论再去解释什麽,都会让事情更加糟糕。
谢怀枭盯着地上哭着像个泪人的白容:“玉儿的命牵扯到大周国,他若是有事,自然有人会来杀你。你好自为之吧!”
言毕,黑金色的袍摆从白容身边擦过,谢怀枭噙着一身冷郁气息离开。
白容愣怔了一刻後,满眼不明的望向王氏:“母亲,怀枭的话语,我怎能听着糊涂呐?”
王氏也糊涂着谢怀枭如此说的意思。
宴商舟为文初处理好伤口,又马上将文初脱臼的手腕治理好。
文初还昏迷着。
宴商舟红着眼,坐在床边心疼的望着文初。
“那个谢怀枭真是个畜生,这般的欺负皇上。”
宴商舟咬了咬牙:“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他的。”

![女配她刀长四十米[七零]](/img/2069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