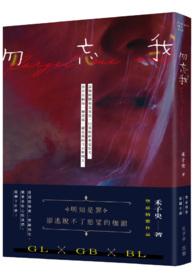富士小说>先生请坐的梗是啥意思 > 东方欲晓(第2页)
东方欲晓(第2页)
又去准备了湿帕子盖在她眼睛上。
纪汝琼是吃晚饭的时候醒的,尽管风月在她眼睛上盖了湿帕子,她眼睛还是肿着。
可见她下午哭的有多伤心。
“怎麽了?”晚饭桌上,风月忍不住问她:“怎麽哭的这麽伤心?”
听见风月的话,纪汝琼身形一晃,豆大的眼泪又开始不要钱的往下落。
断断续续的说:“日本人……觊觎……我家的财産,我二叔……投靠了日本人,一个月前日本人进了我家,我爸妈还有我嫂子……”
纪汝琼後面的话没说,但风月已经了然,脑子里像炸了个响雷,心头猛地像被什麽撞了一下,痛的让人有些承受不住。
风月手里的筷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指尖冰凉。
她想起自己写的那封信,想起信里那些关于春日丶关于孩子的话,原来早就没有了收信人。
纪汝琼还是哭着,断断续续的补充:“当时……消息传来……上海时我哥……在成都,我……我好不容易……才扛下来的消息,我哥回……上海当天……就知道了。”
风月伸手轻轻抚着她的背脊,帮她顺着气,只听她慢慢说:“我哥一蹶不振,饭也不吃谁也不理,没过几天就住了院,靠着营养液续命,我在医院陪了他一个月,医生给我下了七回病危通知书,他差点就死在了这麽好的春天……”
风月听着她的话,微微失神,他与柴霏雪自幼一起长大,这麽多年深爱着彼此矢志不渝,过年的时候知道柴霏雪怀孕他得有多高兴……怎麽偏偏就是这个时候。
纪汝琼馀光看见风月失神,知道她可能是想到了柴霏雪对纪豫行的影响。
但她不知道,纪豫行受的打击,不光有柴霏雪,还有张承霖。
一九三七年秋张承霖牺牲,一九三八年春柴斐雪去世,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两个人在短短半年内先後离他而去。
後来的一辈子他都将在仇恨的笼罩下活着。
一生都再得不到一丁点圆满和幸福。
窗外的桃花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被风卷着落在窗台上,明明是暖融融的春景,却让人心头发寒。
他们这些活着的人,只能在废墟里捡拾起一点温暖,小心翼翼地护着,才能撑过这漫长的寒冬。
风月留纪汝琼在家里住了三天,之後交给她一项重任,把她赶回了上海。
纪汝琼带着风月的任务走时,心里还惶惶不安,她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
但事到如今,她也只能听风月的,成与不成都只能背水一战。
纪汝琼回上海,先是找盛东升打了申请,然後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才终于带着纪豫行登上了去山东的火车。
纪豫行的状态还是很不好,整日萎靡不振,睡不了一个囫囵觉,每闭上眼睛脑海中就全是张承霖和柴霏雪的身影。
纪汝琼带着他到了枣庄他的住处,风月二话没说把岁岁送来了。
风月的想法也很简单,让纪汝琼和岁岁一起陪着他,给他分分心,总也是要好很多的。
起码不让他老是一个人一直陷在过往的梦魇中。
最开始几天,纪豫行看见岁岁,心头那股伤心更浓郁,但在岁岁面前他是怎麽都不可能哭的,他怕惹得岁岁不开心。
後来和岁岁在一处待久了,也慢慢开始舒怀,放下过往所惦念丶追寻的一切,只看眼前实实在在在他身边的岁岁。
人也渐渐好了很多。
纪汝琼也从天天在风月身边哭兮兮,到脸上慢慢开始有了笑颜。
果然还是应了那句话,一个家不管再怎麽空旷丶冷清,有了小孩子总是会热闹丶温馨许多的。
纪豫行和纪汝琼在山东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这三个月间,岁岁学会了喊“爹爹”“娘”还有一句模糊的“嘟嘟(姑姑)”,也慢慢地可以自己走几步路。
纪家的事传到郑明哲和何中华耳朵里,两个人从上海和南方特地跑过来陪了纪豫行一阵儿,何中华回上海後不久,就和那位叫霍瑶的姑娘订了婚,婚期定在来年桃花绽放的三月阳春。
新杰也还是保持着差不多一个月来三次看望岁岁的频率,他这个频率太固定,以至于风月不得不相信——他就是领了张承霖的命令来的。
而至于为什麽张承霖自始至终也没回过家,刚开始风月也心里难受,也无数次怀疑过,可南方的局势越来越乱,纪豫行又负伤在家,他们和她说“因为纪豫行闲着了,所以盛先生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到了张承霖身上”,风月也慢慢的就信了。
外面小池塘里的荷花含苞待放时,纪豫行还是没忘了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回了盛先生身边,回去扛起他在乱世中的责任。
他走的时候风月还挺开心的,一是因为他终于恢复成了那个从前的他,二是因为他回去了,盛东升给张承霖安排的事也能少一点,乱世之中他也总能有口喘息。

![女配她刀长四十米[七零]](/img/2069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