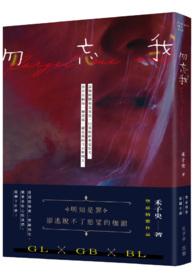富士小说>崩坏之守护律者 > 第1章 人偶师1(第1页)
第1章 人偶师1(第1页)
他们把"懂事"纺成线,穿透你的骨缝,扭曲你的关节。
瞧瞧,现在你跳得多完美啊——
一边跳,一边用缝死的嘴巴,唱着爸爸妈妈最爱听的《乖小孩进行曲》。
「人偶师」,第一幕,第一场。
……
「英雄」不过是垃圾一样的幻想。
他们的存在对于如今的世界是可笑的。
曾经有个浑身邋遢,嗜酒如命的男人嗤笑着对我说。
十多年前,他因幼时的玩世不恭而被捕入狱,同时被家里的人断绝了关系,出狱后自己一个人在外颠沛流离。
而我是他弟弟的孩子。他从亲缘上是我的叔叔。
我的父母因为车祸死亡,爷爷奶奶也早就不在了。
“那两个老东西肯定是被我气死的。”
叔叔在酒后常常这样捂着脸喃喃自语,指缝间漏出浑浊的、不知是泪还是汗的液体。
但下一秒,他又会猛地抬起头,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带着一种似是病态的得意,仿佛这是他为数不多值得“骄傲”的成就。
笑声在空荡破败的屋子里撞来撞去,最后都落在我身上,沉甸甸的。
而我则是默不作声,微笑着给他倒酒,看着他一杯一杯接着喝。
“……真恶心啊,这副笑容,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憨厚老实的家伙吗?”
他忽然转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像是被什么极脏的东西刺到了,“呸”地朝我吐了口唾沫。
恶心吗……
我当时没有去管衣襟上的污秽,我只是用指尖,轻轻摸了摸自己僵硬的脸颊。
肌肉因为长时间的维持已经有些酸痛麻木,皮肤冰冷得像块石头。
他说的一点没错。
在很久以前,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次被嘲笑“没爹没妈的野孩子”,第一次被叔叔揪着衣襟怒视时,我就开始了这项工程。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站在唯一那面布满裂纹、水银剥落的旧镜子前,对着里面那个不言苟笑,眼神淡漠的影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嘴角上扬多少度看起来最无害?
眼睛弯到什么程度显得最温顺?
牙齿露几颗才显得既真诚又不蠢?
为了不被‘讨厌’,
为了不被‘抛弃’,
因为我是‘异类’。
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只有一个坐过牢,成天污言秽语,骂骂咧咧的‘叔叔’。
老师们偶尔流露的怜悯目光,同学们背后压低声音的嘲笑和议论,都让我如芒在背。
我只能用更完美的笑容去回应,用更恭顺的态度去完成值日,用不上不下的成绩去证明我的“无害”,“值得存在”,以及“不出风头”。
我的笑容,是隔绝所有探究目光的城墙,也是麻痹我自己的毒药。
它无关憨厚,无关老实,它只是生存的本能,是现实中开出的畸形而坚韧的花。
在这个世界,「英雄」是不被允许存在的。
在我由于成绩进步,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个奥特曼的塑料玩具作为奖赏时,他从欢喜的我手中一把夺过,将其扔在地上摔成了碎片。
“不准把这种垃圾带回来!英雄什么的,不过是!”
他如此怒吼,随后扬起了粗糙的巴掌。可预想中的掌掴却迟迟没有落下。

![女配她刀长四十米[七零]](/img/2069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