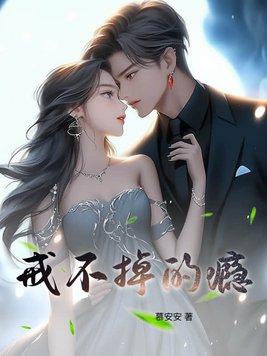富士小说>寒门商途免费阅读 > 第95章 笔耕两载择路杏坛(第2页)
第95章 笔耕两载择路杏坛(第2页)
两年来,秦宇轩的书桌堆起厚厚稿纸。
他在《经济日报》了篇专栏文章,如《开放不是“甩包袱”,本土才是“压舱石”》。
在《中国工业经济》等核心期刊学术论文篇,o余篇政策建议登在《内参》等刊物。
整理表目录时,他才惊觉写下百万字。
深夜台灯、公交上的笔记本、车间访谈,都成了这段时光的注脚。
抉择时刻,心向杏坛
研二下学期,也就是年月的一天,系主任把秦宇轩叫到办公室。
“学校打算破格留你任教,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地方经济研究》。”系主任递过热茶,“考虑一下?”
秦宇轩握着烫的茶杯,一时怔住。
留校是许多人的梦想:工作稳定、环境熟悉、能继续钻研学术。
他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想起两年前的自己。
第一次进菜农老李的菜地,第一次听王厂长诉苦,第一次对着《资本论》彻夜思考。
当晚,他给关中老家打电话。
母亲欣喜:“留校好,稳定还能做学问,适合你。”
父亲却沉默片刻:“你想清楚了?还能像现在这样跑基层吗?”
父亲的话戳中了他的心事。
挂了电话,秦宇轩翻开调研笔记。
里面夹着老李送的萝卜种子、王厂长赠的纪念章、干部手写的联系方式。
这些带着温度的物件,让他想起初心:不是为了表论文,而是让理论走进实践。
接下来几天,秦宇轩反复思量。
他请教导师,导师笑道:“留校是新。你可以把案例带进课堂,带学生做调研。”
导师的话点醒了他。
他想起会议上基层干部对理论的渴求,工厂技术员对政策的困惑,课堂上学生的追问。
留校能成为桥梁,连接经典理论与地方实践,培养更多懂理论、接地气的人才。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同时,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不足:理论体系不够系统,教学方法待创新。
“我还年轻,需要沉淀。”秦宇轩在笔记本上写道。
“留校不是停下,是换种方式成长——讲台上传道,调研中深耕。”
做出决定后,秦宇轩拜访田主任。
“我决定留校任教。”
田主任拍手称赞:“好选择!把实践和理论教给学生,能为陕东经济出力。”
他递过《陕东省六五计划》文件:“这是年批准实施的计划,正全力推进。”
田主任补充道:“你的研究贴合计划中‘协调经济展、提升本土产业活力’的要求,往后多结合计划做研究,能为落地添砖加瓦。”
秦宇轩双手接过文件,指尖抚过“六五计划”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