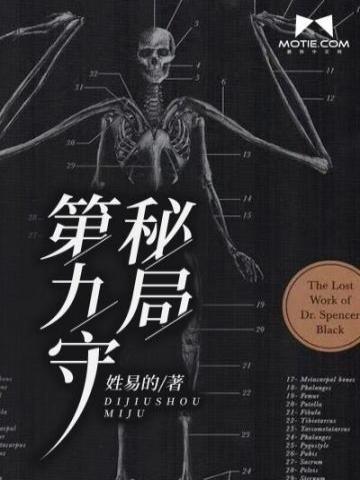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家养丫鬟变王妃 > 第82章 冻伤 晋江文学城(第4页)
第82章 冻伤 晋江文学城(第4页)
挠过以後反而更肿更痒,破了还有脓水。
得了怪病?
还是被文辞报复,中了剧毒?
眼下才十一月中,难道她注定要十二月之前就撒手人寰?
越想越怕,乔婉眠哽咽着穿衣,裹着松垮斗篷往外冲,绣鞋跑掉一只也顾不得捡。
桑耳与爹爹的营房都没有人。她才猛然想起萧越昨日带她去赏雪前交给了他们任务,说是去接人。
等乔婉眠慌里慌张跑到萧越帐门口时,连脸颊也开始痒了!
守在门口的亲卫瞧见是她,对视一眼绕到帐後。
待她赤着左脚闯进萧越营房时,连耳垂都开始发痒。
萧越略显茫然地看着少女甩掉斗篷,一头扎向自己。
烛光摇曳间,但见少女青丝散落肩头,中衣领口歪斜露出半截雪颈,酡红面颊沾着泪痕,赤足发红,犹带碎雪。
乔婉眠哭唧唧将手举到他脸前,道:“萧越!我可能还是要死了!”浑然不觉自己只隔着单薄寝衣紧贴着他的腰腹有何不妥。
萧越抓过她的手,垂眸细看,眼神一凛,“还有哪痒?”
“还有脚……”
“……脸也开始痒了。肯定是文辞怪我骗他,偷偷给我下毒,我会死得很丑吗呜……”
萧越平静:“你不会死,这是冻疮。”
“……”
乔婉眠流了一半的泪尴尬僵在面上。这就是生冻疮?
“可我穿得明明很严实——”她话音戛然而止,眼前忽现雪原上的回忆——自己赤手攥着雪球等它变冰球……不知双足深埋雪中,早冻得麻木。
乔婉眠脸上愈发涨热。
忽觉身子一轻,萧越将她落入里间榻上,耐心解释:“脸上只微微发红,是最轻的;手上肿胀发痒有水泡,是其次,抹药三五天即可痊愈;足下……要看过才知晓。”
他见乔婉眠仍在呆呆出神,更加柔和了语气:“冻疮不是重病,但也极折磨人。是我思虑不周,让你受苦了。来,伸脚。”
乔婉眠却伸手,长睫上挂着粒粒眨碎了的小水珠,可怜巴巴,“你这里有药给我吗?有我就回去自己涂。没有我就忍一晚,明日去找啓束。”
“不必,我这里正巧有药。”萧越将她小靴脱掉,指挥,“往里躺。”
乔婉眠条件反射似的听话,而後猛然发现自己又仅穿着中衣。
-
黯月高挂,北风卷着碎雪叩打窗棂。
室内一豆暖灯,萧越端坐床边,轻轻捉住起半仰少女的小腿。
乔婉眠心蓦地一跳,头脑发懵,浑身只剩高举的脚还在痒。
她挣扎,“萧越,你做什麽……”萧越力道不重,乔婉眠却挣脱不开,只能闺房情趣似的来回晃动,投在墙上的影子格外暧昧。
萧越眸光湖面般平静,满脸的霁月清风,另一手轻轻抓住她脚尖的罗袜,淡声,“怕什麽,”他指尖掠过她脚背青脉,“你刚进长庆侯府时,不就赤脚睡在我湢室中?”
墙影里,纤足倏地躲远。
乔婉眠揪着锦褥往後缩,开始胡搅蛮缠,“那你不懂非礼勿视吗?啊……”在她絮叨期间,另一只脚上的罗袜被萧越褪下。
五根小巧圆润的脚趾红肿得皮肉几乎透明,正不安地拼命蜷缩。
萧越只瞟了一眼就去捉另一只脚,平静道:“手足情况差不多。别挠,破了伤口好得慢。”
他眼底没有侵略性,乔婉眠也安定下来,只全力攥着拳,忍耐铺天盖地的奇痒。
只是她不懂,萧越看似平静的眸底翻涌着灼心烈焰。
褪下後,萧越探身向床头,与乔婉眠呼吸相闻,只略微顿了一瞬间,从枕边摸出药罐,揭开盖子。
清凉苦涩的药味瞬间弥漫,他伸三指搅动膏体,如抚琴弦。
乔婉眠盯着那修长手指在瓷罐中旋抹,忽觉喉间发紧——分明是上药,偏生被他做出几分狎昵意味。
紧接着,萧越恶劣地对她弯唇,从中挖出一抹深赭石色的药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