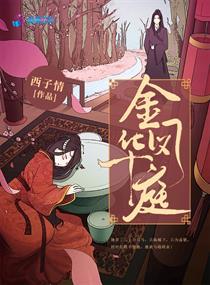富士小说>岁时 > 第31章 笔名撞车风波(第1页)
第31章 笔名撞车风波(第1页)
深秋的午后,阳光透过编辑部明亮的玻璃窗,在磨砂金属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苏念坐在靠窗的工位上,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键盘,目光却始终无法聚焦在屏幕密密麻麻的文字上。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染上深浅不一的金黄,偶尔有几片随风摇曳,缓缓飘落,在地上铺就一层柔软的地毯。这样的景致本该令人心旷神怡,但今天的苏念却无心欣赏。
她的心思早已飘向了那个期待已久的邮件——本期《文学清风》的样刊送达通知。这是她第三次在“青年作家专栏”表文章,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那样令人悸动。前两次使用的笔名“砚念”已经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好评,甚至有读者来信说喜欢她文字中流淌的温暖与真实。这些鼓励像是一盏盏小灯,在她创作的道路上闪烁,给予她前行的勇气。
墙上的时钟指向四点十五分,门口传来熟悉的快递员脚步声。苏念几乎是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向前台。她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那种期待与紧张交织的感觉,让她想起小时候等待期末考试成绩公布的那一刻。
她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指尖能感受到杂志光洁的封面透过纸张传递来的微凉触感。信封上熟悉的“文学清风”四个字让她微微一笑,这是她文学梦想的载体,每一次接触都让她感到无比神圣。
回到座位,她深吸一口气,才慢慢拆开信封。《文学清风》十月刊的封面是一幅水墨风格的秋景图,苍劲的松枝与远山相映成趣,右下角“文学清风”四个行书字挺拔有力。她习惯性地先翻阅目录,找到自己的文章所在页码——第页,“青年作家专栏”。
然而,当她的目光落在那一页时,呼吸蓦地一滞。
两个相同的笔名并排列在相邻的文章标题下方——“砚念”。
苏念攥着刚收到的杂志样刊,指尖不自觉地收紧,光滑的铜版纸页被捏出浅浅折痕。她投稿时精心选择的笔名“砚念”,竟与另一位作者完全重合,连刊登的栏目都紧挨着。这种巧合在文学期刊中实属罕见,却偏偏让她碰上了。
她的目光在两个“砚念”之间来回移动,比较着两篇文章的版面和字数。另一篇《秋声赋》篇幅明显更长,被安排在页面上部,而她的《书窗闲话》则位于下方。尽管编辑已经用心通过排版做了区分,但笔名完全相同的事实依然让她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
“怎么会这样”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偷走了什么珍贵的东西。那个笔名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更是她文学身份的一部分,承载着她的情感与记忆。
她想起一年前选择这个笔名时的情景。那是个雨夜,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她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苦思冥想一个能够代表自己的笔名。她想了很多名字,但都觉得不够贴切。直到目光落在书桌上那方端砚上——那是陆时砚从江南带回来的礼物,墨色深沉,边缘刻着细密的云纹,古朴而雅致。
“砚念”两个字在那一刻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既有着对文字的敬畏,又藏着对赠砚人的缱绻思念。这个笔名像是为她量身定制,完美地融合了她的情感与追求。
而现在,这个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的名字,竟然与他人共享。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秘密花园里突然闯入了陌生人,虽然对方并无恶意,但还是让她感到不适。
“怎么了?脸皱得像被雨浇过的纸鸢。”一个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伴随着刚泡好的热可可的浓郁甜香。
陆时砚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她的椅后,微微俯身看着桌上的杂志。他刚结束下午的课程,深蓝色毛衣袖口稍稍挽起,露出线条流畅的手腕。作为大学文学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总是能在严谨学术与温和待人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
苏念把样刊往他面前推了推,语气带着不自觉的委屈:“我用了好久的笔名,居然和别人撞了编辑说下次投稿得改,可我想了一下午,都没想出比砚念更合心意的。”
她没说的是,“砚”字藏着陆时砚的名字,是她当初偷偷嵌进去的小心思。那是一年前的一个雨夜,她刚决定尝试文学创作,坐在窗边苦思笔名时,目光不经意落在陆时砚送的那方端砚上。砚台墨色深沉,边缘刻着细密的云纹,是他从江南古镇带回来的礼物。“砚念”两个字便在那一刻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既有着对文字的敬畏,又藏着对赠砚人的缱绻思念。
陆时砚接过杂志,目光在两个“砚念”上顿了顿。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页面,眼底渐渐浮现出了然的笑意:“想保留砚字?”他的声音低沉温和,像秋日里缓缓流淌的泉水。
见苏念点头,他指尖在杂志边缘轻轻敲了敲,似在斟酌词句:“那不如加个衬字,比如念砚之?既藏了心意,又和别人区分开,读起来也顺口。”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苏念愣了愣,随即意识到他早已看穿笔名里藏着的小秘密,耳尖瞬间烫。她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念砚之”三个字,钢笔尖划过纸张出沙沙声响。这三个字笔画间像裹了蜜糖,越看越觉得恰到好处。既保留了原来的意境,又添了几分古典雅致。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又往往源自对传统的深切理解与尊重。”陆时砚轻声说道,引用的不知是哪位大家的言论,却恰如其分地抚平了苏念心中的褶皱。
她抬头,正对上陆时砚温柔的目光。他递过热可可,白瓷杯壁温暖适中:“先喝点暖的,要是还想再琢磨,晚上回家我们一起想。”
窗外的夕阳渐渐西斜,橙红色的光芒透过玻璃,在桌面上拉长了两人的影子。那些光影交错着叠在展开的杂志上,两个“砚念”旁,新写的“念砚之”渐渐被暖光染得柔软而明亮。
苏念小口啜饮着热可可,甜而不腻的液体温暖了她的身心。她注意到陆时砚的目光仍停留在杂志上,似乎在仔细阅读那篇同名的文章。
“这位砚念文笔老练,应该是位资深作者。”陆时砚若有所思地说,“你的文章清新自然,各有千秋。”
苏念这才仔细读起那篇《秋声赋》。确实如陆时砚所说,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展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文章中,作者以秋声为引,抒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字里行间透着阅历与沧桑。相比之下,她的散文则更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文字朴实而情感真挚。
“或许这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陆时翻到杂志的目录页,指着上面几十个笔名说道,“每个创作者都会经历从模仿到独创的过程,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他的话让苏念想起自己刚开始写作时的迷茫。那时她常常模仿喜欢的作家风格,字斟句酌地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甚至刻意模仿某些名家的笔调。直到后来,在陆时砚的鼓励下,她才逐渐放下对“像谁”的执念,开始尝试出自己的声音。
记得有一次,她写了一篇模仿某位当代散文大家风格的文章,自觉颇为得意,拿给陆时砚看。他仔细阅读后,温和地说:“写得很好,技巧上也接近了你模仿的对象。但是,我在其中听不到你的声音。”
那句话如醍醐灌顶,让她意识到创作的真谛不在于模仿得多像,而在于表达得多真。从那以后,她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记录生活中的点滴感悟,用最真诚的文字与读者交流。
这次笔名撞车,或许正是提醒她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创作方向。
“你说得对。”苏念放下茶杯,眼神重新变得坚定,“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
陆时砚欣慰地笑了:“正是如此。优秀的创作者往往能够融汇古今,贯通中西,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举例说起几位文学大家的创作历程,他们如何在模仿中学习,在借鉴中创新,最终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苏念听得入神,心中的郁结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编辑部的同事们开始陆续收拾物品准备下班。苏念也将样刊小心地收进包中,决定回家再好好思考笔名的问题。
走出编辑部大楼,秋日的晚风已有几分凉意。陆时砚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外套披在苏念肩上,带着体温的衣服驱散了周围的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