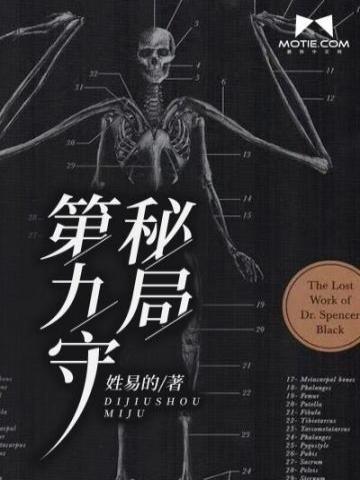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攻略反派们翻车后免费阅读 > 妒意(第2页)
妒意(第2页)
有种慈悲又嗜血的疯批美人的感觉。
裴宁辞闻言却笑,依旧是一如既往地淡:“我知道。”
李婧冉眨了下眼,刚想说他自恋,但裴宁辞却趁着她微微放松时采取了敌退我进的攻势。
她的专注力便都用来感知他的手指了,连呼吸声都窒了片刻,捏着他手腕的指尖紧了几分,有些颤。
裴宁慈仍然神色淡然,在她的耳垂轻轻一吻,低声道:“李婧冉,我不信佛。”
不信佛又为何带佛珠?自然是因为他知晓,她会觉得好看。
他在处心积虑地勾出她心中对他的欲。念。
去除一切委婉的粉饰後,应当叫——让她想睡他。
爱情在裴宁辞眼中当真是个分外简单的东西,他不理解为何有些人偏要将它鼓吹得如此复杂又神圣。
爱很简单,是付出丶承诺和激情。
付出是他为了她放弃了一切的坚守和命数,并且如今强求她同样一无所有地被囚在他身边。
在两人一同在海上漂泊时,他凿穿了他们唯一的舟,抽散了一切的求生希望,只留下一块被他们二人抱着的浮木,让两人的命运被绑定在一起,所能依靠的只有彼此。
承诺是他如今想给她的空前大婚,是她先前口中那些虚情假意的我爱你,是他往後要循循善诱从她嘴里心里榨出来的爱意。
激情是做。
李婧冉好半晌後才平复了呼吸,指尖仍勾着他,声音都有些颤却仍不服输,强撑着维持着脑子的清明:“你不是大祭司吗?怎可能不信神佛?”
裴宁辞闻言只是笑:“确定要在床上谈这些?”
李婧冉见裴宁辞先卸下了这圣人皮囊,也不再嘴硬,喘了口气,掌心用力压着他贴向自己。
裴宁辞垂眸,耳朵俯在她唇边,感受着她温热的气息。
“裴宁辞,先前我教了你怎麽接吻,教了你怎麽沉沦,教了你怎麽在人声鼎沸中同我暗潮流涌。”
她的语气又轻又软,像是一道羽毛,轻飘飘地一寸寸滑过他的皮肤。
李婧冉嗓音含笑,雪腮染绯却姿态闲散,一字一句地在他耳边道:“现在,知道要怎麽做吗?”
裴宁辞似有所觉般垂眸。
她的指尖随意地撩拨着他耳边的流苏,在细碎声响中轻啓红唇:
“戴着耳坠,操我。”
***
李婧冉心想,裴宁辞的确生了个又冷又硬的脾气,着实没那麽讨喜。
但毕竟是她亲手把他堕进红尘的,他从拥抱丶接吻,再到更多,处处都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
门窗紧闭,吹不进满是旖旎的殿内。
沙漏里的沙子在不知不觉地流逝着,不知过了多久,床幔终于被一只冷白的手挑开,勾起。
凌厉的腕骨上还残留着一个不深不浅的齿印。
裴宁辞弯腰捡起地上的外衫,思索了片刻,似是在想这种时候一般应该说些什麽。
他措了会儿辞,低声问她:“饿不饿?”
李婧冉的生物钟原本是很准时的,这些日子被接二连三地打乱,如今打了个哈欠却并没有睡意,半阖着眼懒洋洋地问了句:“哪种饿?”
裴宁辞纵然已经见识过李婧冉很多恬不知耻的话,如今听到她的回应时,金眸还是禁不住轻晃了下。
他眼皮一垂,须臾嗓音清冷地反问:“继续?”
李婧冉有时候也总被裴宁辞冷不丁的话给措不及防地噎住。
先是以前的“做吗?”,再是如今的“继续?”,她心中也会有一丝混合着成就感的隐秘愧疚。
能把一个不染红尘的人教成如今这个模样,她的确是功不可没啊。
其实在大部分时候,裴宁辞不嘴硬时真的很直白,没有那麽多弯弯绕绕,简单明了地说出她想听的话。
只是他总是很吝啬,一句“我爱你”分明那麽容易,但是却宁愿在心里闷坏也不愿意说给她听。
李婧冉往里头挪了挪,十分有富婆姐姐的架势,拍了下床边的空位道:“来,美人儿,陪我再睡会儿。”
她想了想又补充道:“字面意思的丶单纯的睡。”
裴宁辞微挑了下眉,并未言语,从善如流地重新在床沿坐下。
李婧冉踢了被子转了个身子,头枕在他腿上,散漫地伸手去够他的脸。
裴宁辞注视着她半秒,迟疑了下,但还是依着她的意思向她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