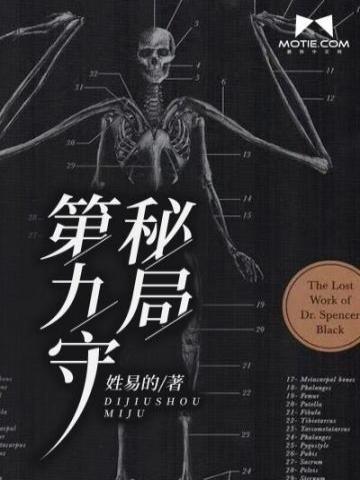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网王之追学姐 > 第 1 章(第2页)
第 1 章(第2页)
他维持着无可挑剔的笑容,再次躬身。
退回後台,喧闹和恭喜声扑面而来。他应付了几句,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准备去卸妆换衣服。
走廊转角,几乎重现了几个小时前的场景。
她站在那里,微仰着头看墙上的演出海报,听到脚步声,她转过头。
四目再次相对。
她眼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惊讶,随即又化为那种平静的礼貌。她对他微微点头致意,像是为又一次偶遇打招呼。
忍足停下脚步,空气里又萦绕起那股冷冽的雪松调,比之前更清晰了些。
他鬼使神差地开口,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丶比平时更低的温和:“在找什麽吗?还是又迷路了?”
她闻言,摇了摇头,顿了顿补充道,“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
很客套的夸奖,忍足却觉得心情莫名好了起来。
“谢谢。”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後的目光带着笑意,“是雪松吗?”
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麽:“嗯。你很敏锐。”
“因为很特别。”忍足他斟酌了一下词句,“像……冬天的森林。”
“不冷吗?”
“不会。”忍足看着她,“很适合你。”
短暂的沉默在走廊里弥漫,却不显尴尬,只有那缕雪松香无声流淌。
女孩先开口,对他颔首:“再见。”
“再见。”忍足站在原地。
他深吸一口气,冰冷的木质香终于彻底缠绕上来,盘踞不去。
他想,或许该去查查,这种香水到底是什麽牌子。
後台的喧嚣像退潮的海水,渐渐平息。
忍足换回了舒适的针织衫和休闲裤,提琴盒斜背在身後。他与最後几位道别的乐团成员颔首致意,推开厚重的隔音门,走向通往外部大厅的走廊。
寂静扑面而来。
然後,极其细微地,一丝钢琴声钻入他的耳朵。
不是录音棚里出来的那种完美无瑕的电子音,而是真实的丶带着木质共鸣和金属弦颤的物理声响。
旋律缓慢,音符之间有着恰到好处的留白,织出一张悠远而哀愁的网,在空旷的演出厅里若有若无地飘荡。
这个时间,工作人员也该清场了,谁还在舞台上?
他脚步顿了顿,几乎是循着本能,像被那无形的丝线牵引,放轻了步子,转向通往观衆席的入口。
巨大的音乐厅内只亮了角落几盏昏暗的清洁灯,穹顶隐没在深邃的黑暗里。
所有的繁华丶掌声丶聚焦的光束都已散去,留下一个庞大而寂静的空壳。
唯一的光源,是一束孤零零的顶灯,打在舞台中央那架漆黑的斯坦威钢琴上。
也打在那个坐在琴凳上的白色身影上。
是她。
忍足在入口处的阴影里停住脚步,屏住了呼吸。
她微微低着头,侧脸的线条在灯光下显得愈发清晰流畅,长睫垂下一小片阴影。
十指在黑白琴键上从容起落,姿态不像是在用力敲击,更像是在抚摸丶在引导,让那些饱含情绪的音响自己流淌出来。
他仔细倾听。
舒伯特?不是。
肖邦?也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