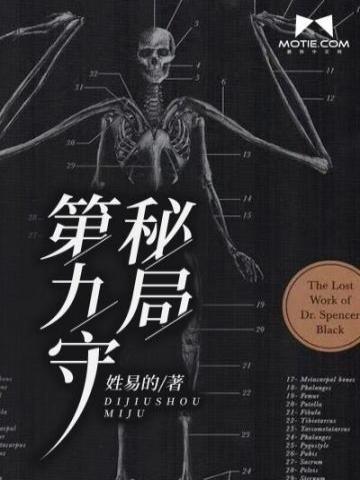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谁还不是主角了gl > 阵痛(第2页)
阵痛(第2页)
“哎,谢仔你就把我放公司吧,我车在公司,看雯姐和周周,要不要你直接送回家吧,大晚上的女孩子打车也怪不安全的。”
周然立即开口:“我不用,我也到公司。”
“那个,我回家,仔哥你方便的话捎我一段吧,老地方,胥宁路那边。”雯姐紧随其後开口道。
“好嘞,那周周你确定要到公司吗?回宿舍去?明天可就直接放假了呀?”
“噢,不是的仔哥,有人来接我了。”
几个人心领神会:“男朋友是吧?”
周然笑了笑,假生气道:“哎呀!别问别问。”
“好好好,不问不问,小丫头真是的,还跟我们保密。。。。。。”
工作结束,假期到来,虽然很晚也很累,但大家还是有说有笑。在公司门口就地散了之後,周然望着马路对面那辆车缓缓掉了个头,来到她这面。
周然抿了抿唇,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明天应该可以休息了?”
“嗯。”
自那天闹不愉快之後,隔天周然确实晾了褚晋将近一天的时间,一直到晚上回酒店才回复她,回复也就是那些例行公事的问话,什麽吃过了,到酒店了,有点累想睡了。。。。。。字里行间的冷淡。
之後几乎每天都是如此,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对吵架的事缄默不提,而让她觉得有些失望的是,她顺着褚晋假装将这件事翻篇,褚晋竟然也就没有再提过。
直到她来问她今天什麽时候到S市丶她来接,周然在婉拒之後她坚持一定要来,周然才心里稍微好受些。
但即便如此,气还是在的,她知道如果要跟褚晋大吵一架,自己一定会是那个主导者,但她想不通的是,为什麽每次主导的人都必须是她,谁都不想成为那个先歇斯底里的人啊!
“放8天?”
“对。”
“需要值班吗?”
“不用,反正有什麽事在家里也能办公。”
“我3号和6号要值班。”
“好。”
像是手机上不能聊一样,在相隔将近半个月没有见面的第一天,两个人居然在互相报备行程。
周然觉得疲惫。
疲惫到闭上眼,泪就能决堤。
“我想了想,你要是不想去医院我们就不去了,我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是我不对,对不起。”褚晋开口,像是在几天的冷静中终于找到了吵架的症结,试图成为那个解铃的系铃人。
周然连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能保证自己在褚晋不发现自己哭的情况下,平静地反问:“你觉得我是因为这个才生气的吗?”
褚晋的沉默让周然忍不住偏首瞥向车窗外,然後抽空擡手抹掉了那源源不断滚下来的眼泪。
“你觉得我是什麽很贱的人吗,我为了让你可怜我,心疼我,我让自己生病?我脑子有问题吧?”
“我不理解,我是做了什麽让你有这样的误会啊?你怎麽能说出这样的话啊?”周然哽咽着。
“我。。。。。。”不知道什麽时候,褚晋竟也在流泪了,抽泣着:“我就是太着急了。。。。。。对不起。。。。。。”
“那你就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为什麽生气,那你为什麽到现在才说对不起,七天了褚晋,我等了你七天,但是你每天都在跟我说什麽?吃饭了吗,睡觉了吗,在工作吗?这些是我想听的话吗?”
“後来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想了想,接了,我以为你会说的,但你没有,还是那些无关紧要的话,我真的特别难过,我都不想跟你讲话,我看到你讲那些话,我就会更难过。”
“我就是不明白,谈恋爱为什麽要这样谈啊,我真就谈了那麽一个木鱼做的女朋友吗,非要敲了才能出点响吗?”
周然一口气将连日来的所有怨气都发泄了出来,她已经不想再装冷静了,她知道她错了,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只会慢慢的内耗内伤,倒不如直接捅破了窗户纸,该怎样就怎样,能谈谈,不能谈拉倒。
“我想的。。。。。。我想等你回来面对面说。”
“那最後先提出来的还是我,那我是不是可以这麽想,如果我不提,你也就不提了,我们就一直这样好了,每天问你吃饭吗,睡觉吗,打游戏吗,那我们可以不做女朋友的,我跟室友也可以这样不是吗?”
“之前也是,说什麽只是负责不负责的,就那麽喜欢来定义我吗?我就想知道,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什麽形象啊?”
“对不起。。。。。。”
多年後,在她们感情真正稳定下来,在一些聚会上玩游戏,总会被人问起,有没有觉得自己和褚晋这段感情没有办法走下的时候。
周然都是说没有的。
这段感情从她的学生时代一直陪伴着她走出少年走入青年,在外人来看似乎稳定坚固到没有什麽东西能够拆散她们。
她们好像天生就该是一对,性格丶爱好丶家境丶生活目标都是那麽恰如其分的匹配,但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其实一切都没有那麽顺利。
很多人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但周然发现,真正让相爱的人分手并不是毕业这一个单一而点状的节点,而是一段以时间为单位的磨搓,是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处境後,人的视野丶思想丶理念丶精力。。。。。。多方位的快速转变。
22岁到24岁里,有多个瞬间,周然都産生了要是实在不行就分开吧的想法。
好像一个“分开”就能解决痛苦的根源,节能减排,一步到位。
但每当産生这样的想法时,她又明确知道,这样不好。
诚如褚晋说的,她放不下这份责任,她无法接受这段感情的无疾而终,她不能只贪图爱情带来的安逸快乐,却又不想接纳那些可能带来的阵痛与酸楚。
更何况,是在更了解褚晋之後的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