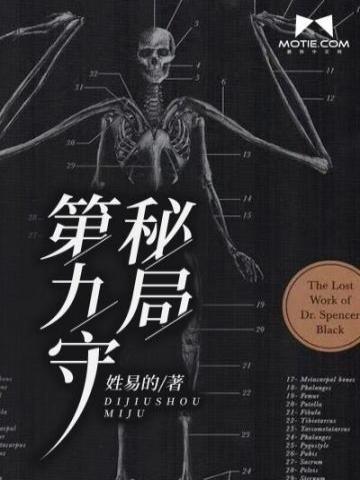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卑微小宫 > 第14章 不甘 伤了手(第2页)
第14章 不甘 伤了手(第2页)
铜镜里原本清澈的眸子多了几分魅色。
“可有不妥?”他又向茅根再此确认。
刚刚还瞪圆了眼的茅根连连摇头:“小主这打扮再合适不过了!”
“对了,小主不换寝衣吗?”他举起手上的薄衣问。
甘草看着窗外的天色摇头。
他的字怕是要扫陛下的兴了,他是有几分想要用身体讨好的心思,可想着昨儿个陛下关于‘教导’的话,他身後有些发紧。
确认了一切妥当了,他才带上写得最工整的纸张跟着内监去往紫宸宫。
……
此时,天边的馀晖还没有散尽,宫人也没带他去往寝宫,而是走向了御书房。
这条回廊比去往寝宫的路更加开阔,但因为不熟悉,让他生出了紧张。
以前他都是天黑来,天亮走,像是某种夜行生物,不好放在阳光下;也只去过寝宫,因为司寝的职责只在燕寝之所。
这是他第一次走向了不一样的地方。
“陛下,甘司寝带到。”内侍停在殿门前禀报。
君王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进来。”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阳光下的陛下,他身上似乎生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温暖。
“虏拜见陛下。”他只怔了一瞬,就继续行礼。
在他还没跪下之前,姒泽就对着他招手了:“免礼,过来。”
时间像是被阳光拉得无限漫长,又像是只有一瞬间,甘草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保持仪态了,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陛下身上。
“字写好了吧,拿来朕看看。”姒泽看着他的宽袖道。
近来朝堂无事,他也有心思关注小司寝了,前面答应小司寝要教导他,此刻自然要履行教导之责了。
甘草骤然醒神,不好意思‘献丑’,也不敢不听,只能磨磨蹭蹭地从广袖中拿出了精挑细选的纸张。
君王接过纸张,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把目光移开:实在是伤眼,五岁的小孩都不会写成这样。
“这字是怎麽写出来的?你给朕写一遍看看。”君王直接把他拉到了书桌前。
丑既然已经献了,他干脆直接摆烂,提笔就开始写。
手腕擡起,衣袖上滑,直接露出了肿胀的手腕。
“你这是怎麽弄的?!”君王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这才想起手腕还伤着,一想起来疼痛就瞬间爆发,原本还能忍的,面对君王关切的神色,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虏也不知为何,只是练了一会儿字,就变成这样了。”他说着就想要遮掩伤处,却被君王强硬地拽着。
练字能把手练成这样?姒泽难以想象,她对着宫人吩咐了一句:“宣太医。”
角落里的宫人快步退下去请太医了。
甘草觉得有些兴师动衆了,可被关切重视的感觉又让他无比贪恋。
“既然这麽要强,就再写一个字,让朕看看是怎麽伤的?”姒泽的心里有一丝生气,也是真想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甘草自然不敢违抗,也不愿意违抗,忍着通,提笔写了个‘甘’字。
他一运笔,姒泽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他手腕内扣,握笔又太紧,若是长时间这麽写,手腕不受伤才怪。
“你这样写,都不累,不痛吗?”姒泽忍不住要叹气了。
少男垂下头语气低落:“虏不想把太丑的字拿到陛下面前。”
这明明时所有臣属都有的心态,但姒泽看着他的神情,心底生出了不一样的感觉,有一点点酸涩,但可以忽略。
她握住了他执笔的手,带着着他的手顺着自己的力道游走:“放松写,认真感受。”
她站在他的身後,半拢着他的身子,两人的气息相容却全无狎昵。
少男感受带着薄茧的大手的每一分力道,然後放松了自己,跟随着君王的力道,仔细地感受着运笔的变化,渐渐地也找到了一些感觉。
手腕仍旧肿着,可被陛下的手腕贴着,疼痛的感觉也没那麽难忍了。
然而,下一刻,君王就放开了他的手:“这段时间就不要写了,等伤好了再说。”
少男有些留恋刚刚行云流水般顺畅的感觉,也有些流连刚刚肌肤相依的感触,但他知道不能奢求更多,只把那感觉牢牢记在心底。
很快,太医就跟着宫人过来了。
“小主的手腕是长时间使用过度照成的损伤,除了敷药按摩外,还要多休息。”太医诊断後下了结论。
姒泽也下了命令,让他少用手。
天色渐晚,君王原本是打算留他侍寝,但看到他手腕就放弃了这个打算直接宣竹韵侍寝。
少男想说,他也可以的。但又怕肿胀的手腕扫了陛下的兴致,只能怏怏不乐地被内监送会了尚寝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