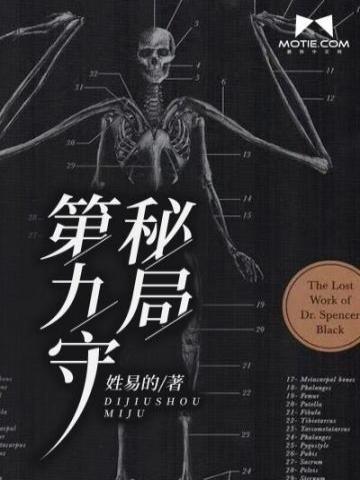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秋天最后一个节日是什么 > 第1章(第1页)
第1章(第1页)
六月底的日头已颇具威慑力,沥青路面被晒得微微软,空气里浮动着令人窒息的燥热,葛正庆推着那辆哑火的摩托车,沉重的铁疙瘩轮胎每往前滚一寸,他心头的邪火就往上窜一截。
葛正庆不怕晒,西北的太阳比这一路的太阳都毒,他晒了整整三十年,连阴天紫外线都不饶人,除了皮肤黑点糙点,他对此其实并没太大实感,太阳于西北人民而言,倒像是一个严厉的大家长,想躲又躲不开,只能学着习惯。
葛正庆受不了的是热。
他依稀记得自己出时是穿着皮夹克的,如今早已脱下捆在了行李包上。
他越往东南方向骑行,尤其是在穿过地图上那条秦淮分界线的时候,那种温吞的湿热便裹了上来,外套成了多余的累赘。
若说西北的热是干烤,那江淮平原的热就是炖煮,天上地下的热气像一口锅扣下来,把人闷在里头,汗水挥不掉,也没那么容易干,把好端端一个人弄得邋里邋遢。
他算是体会到牛肉牛骨被炖成高汤时是怎样一般感受了。
葛正庆的黑色T恤后背洇开了深色的汗迹,他嘴里叼着的烟也燃到了尽头,苦涩的烟蒂味混着汗水的咸涩,让他胸中更加不快,但现在越生气,就越被这天气弄得喘不过气。
终于,他踹下了摩托车的停放架,站在路边捏着烟蒂猛一深呼吸,然后抡圆臂膀,一把将烟头远远地丢了出去,像抛出去一颗手榴弹,炸掉的是一肚子憋闷愤怒,一扭身,吐着烟狠狠给了摩托车的后轮胎一脚。
约莫是和摩托车到了七年之痒吧。
葛正庆耸肩笑了一笑,过后自己却并不觉得好笑,反而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马路上,因着方才苦中作乐的自嘲而真真切切地品尝到了一丝荒凉。
葛正庆是从西北一座名为坊县的县城一路逃亡到这里的,他在那边杀了几个人,走前事情虽然还未败露,但不逃肯定不行。
有个从前跟葛正庆在一个厂里做工的老乡,名字叫罗飞虎的,受过他不少接济,后来他家里老妈生病住院,垫底的钱也全是葛正庆出的,几年前罗飞虎南下到这里,二人的联系一直没断,据说如今是混出了些许名堂,也算个知恩图报的好人,那天在电话里,他听葛正庆谎称在老家得罪了地头蛇,往后恐怕不好找活计了,当即就拍胸脯表示你来我这里,保不了一世,保你一时也够了。
摩托车刚抛锚的那会儿,葛正庆给罗飞虎打了个电话,但是没人接,他被晒得没了耐心,此时又在逃命,根本等不得,了条信息过去之后,一个人愣是梗着脖子推着车,往前走了二里地,好不容易看见蓝色的路牌了,现离县城居然还差二三十公里。
葛正庆从包里拿出毛巾擦了擦汗,弯下腰,对着后视镜抓了抓自己汗湿的短。
他现在已是一脚跨进而立之年,这张曾经在同龄人里太显成熟的脸,在大家都到这个岁数以后反而拥有了一种抵抗衰老的能力,一样都是三十岁的男人,他看着就是要年纪轻些,带着点轻浮但无伤大雅的俏皮,尤其是一双眼睛,虽是单眼皮,却不觉得小,他的上眼睑尾端很长,和内眼角一样微微向下垂,但到了下眼睑的位置,尾端又自顾自往上飞起,人就长了一副狐狸相,加之他口裂长,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时更是坏得厉害,约莫是狐群里面最不老实的那一只。
葛正庆把毛巾挂在脖子上,重新站直身体,掐起腰四下里张望,这地方除了庄稼,别说车子,连第二个会喘气的都找不到,他干脆蹲下来,手肘搭着膝盖,借摩托车的阴影抵挡部分热气。
幸而罗飞虎的回电如及时雨一般降临,他解释说方才在睡午觉,没听见,让葛正庆别急,他问人要了车钥匙就来。
没过半个小时,一辆黑色的皮卡从对面行驶过来,在马路上调了个头,停在了摩托车的正前方。
罗飞虎是个长相周正的青年,门牙微凸,耳朵向外招着,听老人说这种耳朵最是来福,总之,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气洋洋的。
罗飞虎从驾驶座跳下来,打开尾门,爬上车斗将里面的斜坡板放了下来,两个人一推一拉,摩托车就轻轻松松地上去了。
待等关上车门,空调一打,可算感觉到了凉快,葛正庆又拿毛巾擦了把脸,然后是脖子,手臂,最后撩起短袖,探进去擦过胸口和腹部,一改私下里不耐烦的模样,对罗飞虎笑道“热。忒热了。亏你能在这块儿地上扎根。”罗飞虎笑了笑说“住习惯就好了撒,我最开始来,到了夏天真是恨不得裸奔才好,汗全捂在身上,到处起得都是痱子——听歌不?”
罗飞虎打开了车载收音机,接通电源后按了那个标着“cd”的按钮,机器内部先是传来了一阵沙沙的读碟声,在短暂的沉默过后,响起了熟悉的舞曲前奏,是韩国女歌手李贞贤的《哇》,罗飞虎翻来覆去怎么听也听不腻。
眼下过去的歌和过去的人都在,罗飞虎颇有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受,一边开车一边自言自语道“那会儿大街小巷都爱放这歌,尤其是迪厅,当时我跟你,还有其他几个兄弟,一下班,出了厂子就要往迪厅跑……”
葛正庆听着,觉得罗飞虎似乎并没有打算得到什么煽情的回应,便也没插嘴,他抱着胳膊看向窗外,只有头在本能地随着音乐小幅度地点动。
皮卡载着两个旧相识和一段聒噪的往事,沿着公路继续向县城方向驶去,车窗外的风景快流动,看似无垠的田野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抛在身后,路边的行道树变得稠密,枝叶肥厚,绿得暗,蒙着一层从田野带来的细尘,远处出现了疏疏落落的鱼塘和低矮楼屋,而在更远的地方,一座座工厂厂房的轮廓连绵起伏,像镶嵌在绿色海洋边的礁石。
罗飞虎晃的幅度更大,从前他就是最爱热闹和跳舞的人,他快扭头看了眼窗外,指给葛正庆看“那边是开区,这几年搞得很大。”
车轮碾过路面晒软的沥青,出黏腻的声响,路上终于有了人烟,两旁大多是农村自建房,屋顶铺着红瓦片,墙壁上贴着白色或米色的瓷砖,一些人家的屋顶上竖着太阳能热水器,在烈日下反着刺眼的光。
临街的店面招牌五颜六色,但打印的图案在整日的风吹雨淋下已变得模糊黯淡,都是些五金百货、理头理、电动车专卖的字样,歪斜的公交站牌旁的候车亭里,蹲着坐着几个等车的人,正无精打采地摇着扇子。
皮卡驶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水泛着浑浊的绿意,水流缓慢。
过了桥,景象便陡然不同了,路面宽阔起来,是双向四车道的水泥路,虽然有些地方已经龟裂,但气派是有的,路中间立起了隔离栏,显示着这里的秩序与郊野的不同。
路两旁的建筑不再是零散的自建房,而是成排的、样式统一的五六层高的楼房,楼下是各式店铺,招牌弄得规规整整,网吧、服装店、小餐馆、移动营业厅……一应俱全,人也随着这景象的热闹而展现出了一种蓬勃的朝气,各式各样的声音和景色混杂在一起,让在路上逃亡,吃遍了各种风沙的葛正庆久违地感受到了一丝松快和新鲜。
这里与他熟悉的西北小城截然不同,西北是粗粝的、开阔的,色彩是黄土的褐与天空的蓝,但在这里,一切都是湿润的、拥挤的,色彩是各种层次的绿,夹杂着瓷砖的亮白和楼房的灰调,像一位柔情却充满潮湿哀怨的的女子。
这种陌生感并未让他感到不安,反而像给他刷上了一层暂时的保护色,将他与遥远的西北,与那几桩血腥事件隔离开来。
他需要这种喧嚣和陌生来淹没自己。
你要是感覺不錯,歡迎打賞TRc2ous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