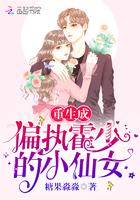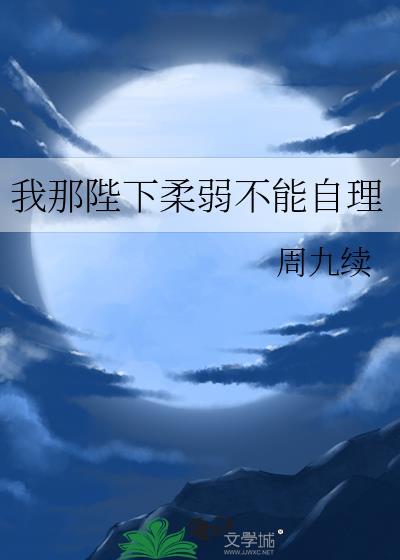富士小说>破帷免费 > 第21章 墨是血煮的(第3页)
第21章 墨是血煮的(第3页)
他这个断了根的宦官,本不该有这些念想,可那一刻,他却觉得,“宦官无子,然天下清流,皆可为嗣。”
他下定决心,冒着风险,私自从库房里拨了一批印错作废的公文纸,命人仔仔细细地在上面盖满了“作废”的大红印章,然后差人送到了槐市那个相熟的老掌灯手里。
老人收到纸,什么也没问。
他连夜动手,就着一盏油灯,用裁刀将那些盖满红印的纸张一张张裁掉边缘,留下中间干净的部分。
刀锋划过纸面,出“嚓嚓”的轻响,像秋叶落地。
一夜下来,他裁了整整三百张可用的纸,一双老手被锋利的刀口割得全是细密的伤痕,有些纸的边缘,还浸染上了一点暗红的血迹。
林昭然见到那摞带着血边的纸时,眼眶一热,便要屈膝跪下。
老人却一把将她扶住,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一股明澈的光:“姑娘,使不得。灯要亮,总得有人在旁边添油。我这把老骨头,也就能出这点力气了。”
有了纸,林昭然写得更快了。
第五日,她已经整整三日三夜没有合眼。
困到极致时,她便用冷水浇头,水珠顺着额滑落,滴在脖颈上激起一阵战栗,让她短暂清醒。
手中的炭条,因为用力过猛,已经折断了三次。
陈砚秋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几次三番劝她停下,她却只是摇头,一字一句地说:“他们要我沉默,我偏要写到声嘶力竭。”
她奋笔疾书,忽然,笔尖在布纸上猛地一顿。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击中了她——她忆起前世那些为了争取权益而罢课抗议的教师,忆起那些贴满校园的、来自学生们的声援信,那是一种集体的呐喊,是知识在压迫中自我组织的形式。
她不能只做那个唯一的答题人。
她深吸一口气,心中豁然开朗,提笔在《答问续编》的末尾,写下了新的一行字:“诸君若心有惑,意有不平,亦可自写《我之问》,投于槐市米行后巷之问匣。吾虽力竭,见问,必以赤诚答之。”
此言一出,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涟漪。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次日,那只简陋的问匣里,竟然被塞进了上百张纸条。
有老农用歪歪扭扭的字迹问:“一年的束修,到底该收几文钱才算公道?”纸面粗糙,墨迹晕开,像是握笔的手在颤抖。
有大户人家的婢女托人代笔问:“我的妹妹,也能有机会识字读书吗?”字迹娟秀却拘谨,仿佛怕写错一个字就会被责罚。
甚至,还有一张折叠工整的信笺,上面是崔玿清隽的笔迹:“若革新之日终至,我辈当何为?”墨香清冽,字字如刀。
林昭然看着这些或粗糙或雅致的问句,感受着其中蕴含的、鲜活的渴望与信任,疲惫的脸上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
她提起笔,蘸了蘸仅剩的墨,一滴殷红的血却从她冻裂的指缝中渗出,悄然滴落在纸上,晕开一朵小小的、倔强的红梅,带着铁锈味的温热。
当夜,她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
她伏在案上,口中不断溢出鲜血,那只握了五天五夜炭条的手,却依旧紧紧地攥着,仿佛那是她唯一的武器。
窗外,阿阮的歌声正唱到最高潮的那一句:“墨尽时,血来煮;声断处,魂不伏。”
郑十七惊惶地将她抱上床榻,回头时,泪眼模糊地看见,书案上,她写下的最后一封回信,正是给崔玿的。
上面只有一行字:“崔君问:当何为?答曰:先为一真人,再谈经世礼。”
他将那封信笺轻轻放回案上,叠在厚厚一沓已回覆的问答旁。
屋子里静得只剩下林昭然微弱的呼吸声,像随时会熄灭的烛火。
然而,郑十七并不知道,就在这片死寂笼罩着小院时,门外那只由旧米箱改造的问匣,正被一只又一只伸来的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悄然填满。
喜欢破帷请大家收藏:dududu破帷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