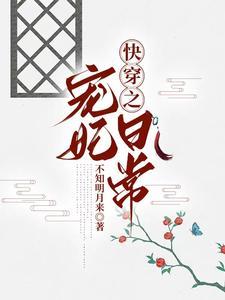富士小说>破帷什么意思 > 第32章 风起青帷(第2页)
第32章 风起青帷(第2页)
枯叶浮在水面,被晨风吹得轻轻打转。
“此议若出我口,礼律司能指我附逆。”他又低头看了眼书里的残页,墨字在光下泛着幽光,“但……”他从袖中摸出枚铜印,压在《礼记正义》上,铜印微凉,带着金属的沉实感,“若由‘民间自’……”铜印抬起时,书页上多了方“太学赵记”的朱印,红得沉静,“或可存一线生机。”
暮色漫进米行密室时,林昭然的笔在宣纸上顿住了。
密室很小,梁上还挂着几串陈米,霉味混着烛火的焦香,在鼻腔里织成一层薄雾。
她面前摊着刚写了一半的《补遗讲章程》,墨迹未干,“凡有才学者,不论出身”几个字被烛火映得亮,像在黑暗中燃烧的火种。
韩霁蹲在门边,炭笔在墙上沙沙作响,画着城南槐市的地形图,笔尖断了一次,他轻轻吹了口气,灰屑飘散在空中。
阿阮坐在窗台上,盲杖靠在身侧,指尖轻轻拨弄琴弦,《启蒙谣》的调子像条细流,从她指缝里淌出来,清越而微颤,像风过竹林。
“明日你以‘陆门复名’之身,当众呈请备案。”林昭然把章程递给韩霁,见他接过时手在抖,纸页出细微的沙响。
“若被拒呢?”他问,声音里带着年轻人才有的急,像绷紧的弦。
林昭然望着窗外——阿阮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落在青石板上,像株在风里摇晃的树,枝叶婆娑。
“拒了,百姓自会问。”她轻声说,声音像落在水面的叶,“问为何连讲一堂课都要许可,问为何寒士的学问不如一块备案的木牌……”她咳嗽起来,用帕子掩着嘴,再拿开时,帕角洇着点淡红,像雪地里落了一瓣梅。
到那时,裴大人的铁令,反成了最好的火把。”
韩霁忽然站起来,章程在他手里出沙沙的响,像风掠过枯草。
他望着林昭然苍白的脸,又望了望阿阮被月光照亮的侧影,忽然把章程往怀里一揣:“我知道了。”他说,声音里有了热乎气,像冻土下涌动的泉,“我明日一早就去。”
林昭然靠在椅背上,看着烛火在韩霁的后颈投下跳动的影子,像一只振翅欲飞的蝶。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咚——”的一声,像颗种子落进泥土里,沉沉地扎下根。
她摸了摸袖中阿阮塞进来的铜炉,还温着,热意透过布料,熨帖着腕骨。
明天午时会生什么呢?
她想。
或许是礼律司的朱门紧闭,或许是百姓围在门前窃窃私语,或许是韩霁的膝盖压在青石板上,把章程和联保书捧得老高……
烛火忽的晃了晃,她望着案头未写完的章程,忽然笑了。
(次日卯时三刻,韩霁在米行后院用新汲的井水洗了把脸。
他把《补遗讲章程》和三张监生联保书仔细卷进竹筒,系上陆门特有的青竹绳。
当他推开院门时,晨雾里已经站了七八个扛着扁担的百姓——是昨夜在石阶下举火把的人,手里还攥着抄着《启蒙谣》的纸页。
)
林昭然是被阿阮的琴弦惊醒的。
医舍后窗的阳光正漫过她的手背,暖意像一层薄纱覆在皮肤上,阿阮的盲杖倚在床头,琴弦却不在膝头——那声音是从廊下传来的,《启蒙谣》的调子被揉得更碎,像落在青石板上的雨珠,清冷而零落。
她撑起身子,看见阿阮正站在院门口,指尖拨着临时绷在竹片上的弦,弦音微颤,身边围了七八个街童,每人手里都攥着皱巴巴的纸页,纸角被汗浸得软。
“阿姐醒了?”阿阮耳力极灵,转身时间的木簪闪了闪,映出一道微光,“韩公子的事,郑十七刚捎了信来。”
林昭然的手指在被单上蜷了蜷,布料粗糙的触感从指尖传来。
她早料到会是这个结果,可当“礼律司拒了”四个字撞进耳朵时,喉间还是泛起腥甜,像有血在喉管里翻涌。
她接过阿阮递来的药盏,苦汁漫过舌尖,舌根一阵麻木,药汁滑入喉咙时,灼得像是吞了火炭。
忽然听见院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是郑十七,青布短打沾着槐市的米糠,额角还挂着汗,气息粗重。
“韩公子还跪在礼律司门前。”他喘着气,声音颤,“谢大人立在阶上,说‘国子监讲席自有定制’,又说寒生妄议制度是乱阶。”他从怀里摸出半块烤饼,掰成两半分给街童,饼皮焦脆,碎屑落在地上。
“后来有个小娃举着《代答录》问:‘阿阮姐姐教我们识字也要批文吗?’谢大人脸都白了,让差役抢了章程就关门。”
林昭然望着窗台上阿阮新晒的艾草,叶片边缘被晒得卷起,像被火舔过的纸,散出更浓的苦香。
她把药盏搁在案上,药汁在青瓷里晃出细碎的涟漪,映着窗外的光,像一池碎金。
“去把笔墨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