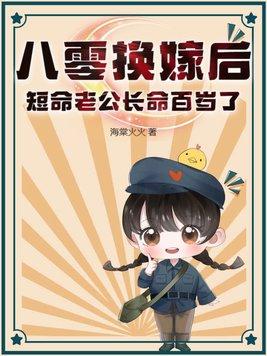富士小说>破帷和巾帼混音 > 第108章 灰蝶扑灯(第2页)
第108章 灰蝶扑灯(第2页)
信纸上的茶渍晕得恰到好处,像被海风腌过的旧物;字迹的颤抖里带着股倔强,倒真像极了他在《遗老诗钞》里见过的前朝太史令笔法。
最妙的是那半枚铜钱——“永贞”二字虽残,却让他想起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去祭前朝皇陵,在断碑前拾到的半块瓦当,上面也刻着同样的年号。
父亲当时说:“那是不肯低头的人最后的年号。”
“大人。”孙奉捧着个檀木匣进来,脚步轻得像怕惊扰了夜,“柳娘子送来的‘灰蝶图’,说是按您从前的吩咐,走密道递进来的——三年前您便在绣坊地下埋了暗格。”
沈砚之掀开匣盖,三幅素绢次第展开。
其余九幅尚在途中,信鸽正穿行于夜色。
第一幅上,半片“答在天下”的残页,“答”字左半像被刀劈裂,右半却隐在绢纹里,若隐若现。
他的指尖轻轻抚过那道裂痕,忽然想起启蒙先生的话:“字断意不断,方为真文脉。”
烛火“噼”地爆了个灯花,火星溅落,像一颗坠落的星。
接下来的三日,十二州的消息如星火燎原。
江州急报送抵时,正是破庙烛影最深的子夜。
信上八字:“学宫灰烬未清,童生聚于阶前。”
她将信笺折成纸蝶,轻轻放在案头的“灰蝶图”旁。
纸蝶的翅膀掠过“答”字残痕,像是要替那个被烧掉的“在”字,补上最后一笔。
“备马。”她对门外候着的随从说,声音里带着久未有的锋锐,“去江州。”
林昭然的青骢马在离学宫半里处打了个响鼻,鼻息喷出白雾,带着草料与焦土混杂的气味。
她翻身下马,将缰绳交给随从时,指尖触到马颈上未褪尽的汗渍——这马是从州府快马换班骑来的,连喘息里都带着焦土味。
学宫的影影绰绰在暮色里浮出来时,她先闻到了那股味。
不是新燃的焦糊,是烧透的纸灰混着湿土,像块浸透了墨的破布,闷在鼻端,久久不散。
她脚步顿了顿,看见学宫门前的石狮子腿上还挂着半片未烧尽的书皮,黄纸边缘蜷成黑蝴蝶的形状,在风中轻轻颤动。
又过两日清晨,程知微的快马再次撞翻门口瓦罐。
他掀开门帘,额角的汗珠子摔在青砖上:“昭然!苏州书驿传来消息,顾侍郎家的三公子把‘灰蝶图’藏在玉扳指里,说‘观之如见天意’!”
林昭然正在理阿阮送来的命题草稿——盲女以指尖刻痕于特制蜡板,每道凹痕深浅有序,林昭然依其节奏落笔,每一字皆经三次触摸方定。
她抬头时,程知微又抖出张纸条:“还有杭州,王御史的孙子在书院里哭,说他祖父当年靠关节中举,如今看这图,背上像扎了根针。”
“孙奉那边呢?”林昭然问。
话音未落,庙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孙奉掀帘进来,手里的茶盏还冒着热气——他总说破庙的茶“有野枣香”。
“国子监的公子们昨夜聚在西斋。”他压低声音,目光扫过案头的命题纸,“我躲在廊下听,有个穿月白锦袍的哭着说:‘若我生寒门,连求个问的资格都没有么?’另一个拍他肩膀:‘不如我们去求双盲誊录,把关节堵了,也算替祖宗赎个罪。’”
夜更深时,破庙里的烛火次第亮起。
柳明漪在补阿阮命题稿的边栏,针脚细密得像雨丝;程知微翻着礼部旧档,把“双盲誊录”的条例抄了又抄;阿阮坐在最中间,面前摊开十数张空白考卷,指尖轻轻抚过纸页,像在摸一群待哺的孩子。
林昭然站在门口,望着庙外的星空。
风里飘来若有若无的墨香,是书驿的人在连夜拓印“灰蝶图”。
她摸了摸袖中,柳明漪不知何时把守拙留下的瓦当缝了进来,粗粝的陶片贴着皮肤,像块烧过又冷却的炭。
“昭然。”程知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考题都誊好了,该密封入匣了。”
她转身时,看见案头摆着个枣木匣,匣盖雕着未完成的灰蝶——是柳明漪白天刻的。
程知微捧起考卷,一张一张放进匣里,最后压上阿阮的命题稿。
当匣盖落下的瞬间,烛火忽的一跳,将“若我生寒门”的字迹投在墙上,像道裂帛的光。
林昭然伸手按住匣上的铜锁。
锁扣冰凉,却让她想起三日前学宫外的火堆——那些被烧碎的字,此刻正躺在这匣里,等着三天后的启封。
她望着窗外渐起的晨雾,轻声道:“这一匣,不是考题。”
“那是什么?”柳明漪停了针。
林昭然笑了,目光穿过晨雾,投向看不见的紫宸殿方向:“是面镜子。照一照,这世道敢不敢看自己的样子。”
枣木匣的铜锁“咔嗒”一声扣上时,东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
喜欢破帷请大家收藏:dududu破帷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