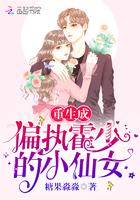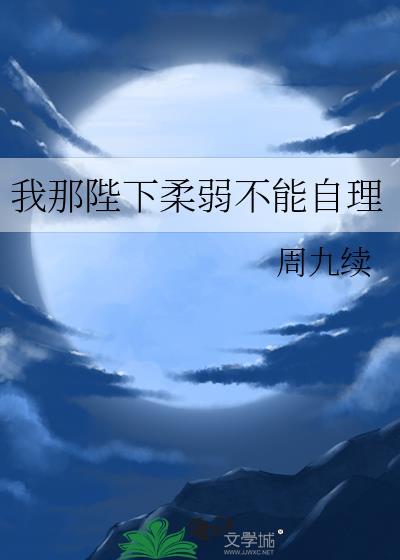富士小说>破帷和巾帼混音 > 第218章 草知道该往哪儿长(第2页)
第218章 草知道该往哪儿长(第2页)
林昭然摸出枚铜钱买水,商贩却推回来:“不用钱。您要是往京西去,替我捎句话——程小先生在驿站等信呢。”
她顿住。
程知微?
那个总在算筹袋上磨出毛边的小吏,那个说“问若有骨,自会立”的年轻人。
她想起前月收到的半片《礼典》拓本,拓本背面用极小的字写着:“京西驿站,草编问字覆马鞍。”
江水在脚边打了个旋,卷走片柳叶。
林昭然望着柳叶漂远,忽然听见江风里裹着细碎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织机上穿线,梭子来回,吱呀轻响。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她顺着声音寻到江边的竹棚,竹棚里立着台老织机,织机前坐着个盲眼老妇,手指正摩挲着岩壁上的盐晶——那些盐晶并非天生而成,是几十年前被贬至此的女织工,用指血拌海卤,夜夜描摹,死后族人继续续写。
每涨一次潮,她们就重新蘸水勾一遍笔画,年复一年,盐层叠压,字迹竟比石刻还深。
如今那四个大字清晰可见:“谁定咸淡?”,潮水印过,盐粒反光,字迹反而更亮。
“柳娘子的‘潮音纱’要来了。”老妇突然开口,指尖停在“淡”字的最后一点上,“我织了半辈子‘回声纱’,总盼着有人应。现在才明白,最响的问,是没人听过也在长的。”
林昭然没说话。
她见过柳明漪的“回声纱”,纱上织着被礼教压碎的“不敢问”,每根丝线都缠着半枚蚕茧。
可此刻岩壁上的盐字,比任何纱都更烫——盐是日晒风吹熬出来的,咸是苦役们的汗浸出来的,这“谁定咸淡?”,是用命在问。
日头偏西时,林昭然在山坳里歇脚。
她解下布囊当枕头,刚要合眼,忽闻山风里有焦糊味,混着一丝墨香,钻入鼻腔,像旧书阁失火时的气息。
抬眼望,南边的山梁上腾起股青烟,火舌卷着纸灰往天上蹿,灰烬打着旋,像一群黑蝶。
她认得那烟——是烧《礼典》的味道,墨香混着纸灰的苦,和当年太学藏书阁走水时一模一样。
可这次的火不一样。
她站起身,眯眼望去,火塘边有件褪色的官袍,玉带扣在火边闪着暗黄的光。
那是沈砚之的玉带,先帝亲赐的“山河同寿”纹,她在朝堂上见过无数次,每次都像块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冰。
此刻玉带扣上沾着草屑,火舌舔过官袍的金线,竟蜷成个“问”字的形状。
“我不是在烧书……是在还火。”
风卷着火苗的噼啪声,送来句低哑的话。
林昭然望着那火,想起沈砚之在《追缉令》上画斜线的夜,想起他解玉带时指节的颤抖。
原来最硬的冰,也会被草籽扎出缝来——南荒古道的石缝里,“问”字草不就是这样,把千年的岩板都顶裂了么?
暮色漫上山头时,林昭然又上了路。
江面上飘来纤夫的号子声,“嘿哟——嘿哟——”的调子里,像是裹着点新东西。
她站在江滩上望,见远处的漕运码头泊着艘大船,纤绳绷得像根弦,几十个纤夫弓着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脊梁流进衣领。
号子声又起。
这次她听清楚了——在“嘿哟”的间隙里,有若有若无的尾音,像是“问”字的余韵,被江风揉碎了,又拼起来。
林昭然摸了摸间的桑叶,叶脉已经干了,却还保持着原样。
她沿着江滩往码头走,麻鞋踩过“问”字草的叶尖,草叶在脚下轻响,像是在应和那若隐若现的号子。
前面,漕运码头的灯笼次第亮起,把江水染成一片暖红。
喜欢破帷请大家收藏:dududu破帷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