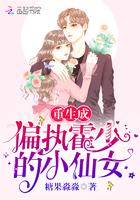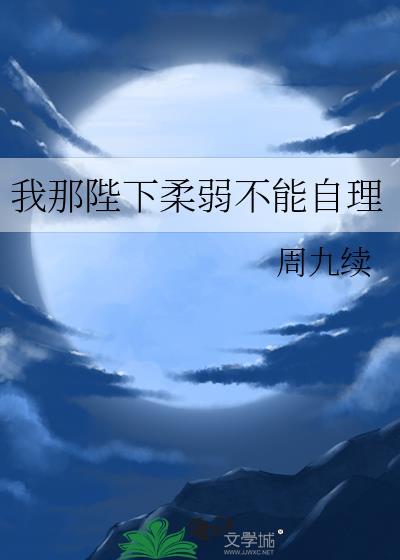富士小说>破帷和巾帼歌曲有什么不同吗 > 第37章 火种南飞(第2页)
第37章 火种南飞(第2页)
船,顺利启航。
与此同时,江岸边的草坡上,绿耳正带着一群半大的孩子,将一只只写着字的纸鸢放上天空。
南风强劲,纸鸢争先恐后地向着江心飞去。
其中一只白色的纸鸢,或许是线不够结实,被一阵突来的旋风卷断了丝线,打着旋儿,竟不偏不倚地挂在了那艘官船高高的桅杆顶上。
“字是光”三个墨色淋漓的大字,在江风中迎风招展,像一句无声的宣告。
岸上,船上,无数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那名差头仰着头,久久地注视着那三个字,脸上的神情变幻莫测。
许久,他忽然扭头对身边一个识字的下属低吼道:“取笔来!”
众人愕然间,只见那差头竟命人将自家船上一面备用的小帆铺开,他自己则抓过毛笔,蘸饱了墨,一笔一划,极其认真地在粗糙的帆布上写下四个大字:“我也识字。”
高处,林昭然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她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舟影,望着那漫天飞舞、如星辰般的纸鸢,忽觉盘踞在心口许久的那股“异世灵光”带来的刺痛,竟悄然消解了。
那股力量不再是割裂骨肉的利刃,而是化作了一股暖流,温柔地回转于四肢百骸。
她缓缓回到室内,取出亡师留下的那本残卷,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
她以指尖蘸墨,笔锋落下时,却不再是仿徨与叩问。
“老师,火种已南飞。”
“他们,不再等一个虚无缥缈的答案了。他们……开始写自己的书。”
墨迹未干,一缕微风不知从何处穿过纸页的缝隙,轻轻卷起了书卷夹层里,那片来自她故乡的、早已化为灰烬的残页。
那片焦灰,如被赋予了生命,化作一捧细碎的星雨,飘出窗外,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南方。
当夜,紫宸殿的烛火彻夜未熄。
沈砚之展开了刚从荆州送来的南行密报。
上面写着:荆州府沿岸,已有童子成群,于码头、田垄间背诵《答天书》之句。
守令非但未曾禁绝,反而在城中几处要地,自掏腰包,设立“夜读角”,供船工脚夫夜间识字。
他沉默了片刻,吩咐道:“取‘补遗讲’的章程抄本来。”
孙伯很快取来。
沈砚之翻开那本记录着讲士身份来历的名册,在空白的页上,亲提朱笔,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两个字:韩霁。
而后,他在其下批注:准录,待考。
孙伯眼中的惊骇,比白日里见到“载心南行”时更甚:“相爷……亲批一名民间讲士入册?这……这不合礼制!我朝百年,从未有过先例!”
沈砚之没有回答。
他起身,走到窗前,恰好望见一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纸鸢,拖着一缕仿佛灰烬凝成的尾巴,如暗夜流星,悄然掠过宫殿高耸的飞檐。
他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语:“孙伯,你看。这一回,火没灭。”
三日后,城南槐市。
一座崭新的讲坛在废墟上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加宽敞坚固。
韩霁一袭青衫,立于其上,手中展开的,正是那份沈砚之亲笔批注过的讲士名册。
他环视台下,那里坐着捧册聆听的绿耳,闭目养神的老申,还有拨动琴弦、为开讲酝酿气氛的阿阮。
更多的人,则是闻讯而来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
韩霁深吸一口气,朗声道:“今日,补遗讲第一课,不讲天,不讲地,我来讲——何为师道!”
台下,一片寂静。
风过处,讲坛后墙上新贴的《答天书》七篇,纸页被吹得微微颤动,在夕阳的余晖里,真如无数只振翅欲飞的素蝶。
而在遥远的紫宸殿深处,那片被妥善收藏于素绢之上的焦灰,静静地躺着,映着灯影,仿佛仍在无声地燃烧。
春风得意,吹绿了江南岸,也吹动了紫禁城里,那些执掌礼法的老人们落满尘埃的官袍。
他们或许听不见南城的喧嚣,却总能嗅到风中那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一场酝酿已久的春雨,似乎就要落下,只是无人知晓,它会滋养破土的新芽,还是会冲刷掉墙上那些刚刚写就的墨迹。
喜欢破帷请大家收藏:dududu破帷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