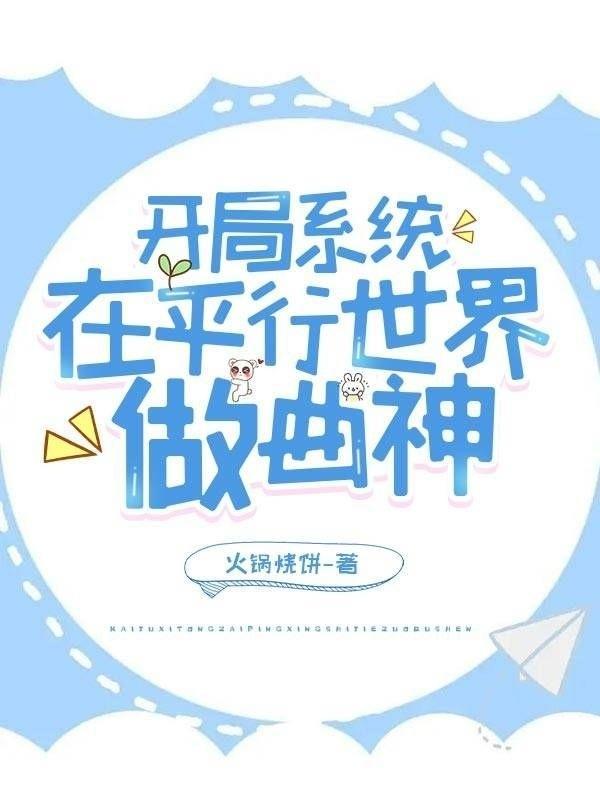富士小说>快穿谁还没个好爸爸最新无弹窗 > 第103章(第1页)
第103章(第1页)
李侍郎皱起眉头:“何事如此惊慌?成何体统!”
“爹!您还不知道吗?靖远侯府……沈家……他们要让沈聿肩祧两房,要娶那个新寡的苏弄月!”李嫣然哭诉道,声音哽咽,却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李侍郎与夫人对视一眼,神色都凝重起来。这事他们隐约有耳闻,但没想到竟是真的,而且女儿反应如此激烈。
“竟有此事?”李侍郎抚须沉吟,“肩祧两房,倒也是沈家无奈之举。长房无后,沈聿确是合适人选……”
“什么合适人选!”李嫣然激动地打断父亲,“那沈弄月不过是个寡妇,凭什么?沈聿是侯爷,是世子!怎能娶一个寡妇为正室?即便是肩祧,也是辱没了门楣!女儿……女儿……”她说着,泪水涟涟,扑进母亲怀里,“女儿心意,爹娘难道不知吗?我非他不嫁的!”
李夫人心疼地搂着女儿,看向丈夫:“老爷,嫣然说得不无道理。那苏弄月门第虽也不低,但毕竟是再醮之身,如何配得上靖远侯正室之位?更何况是肩祧两房,这……这日后说起来,岂不是让嫣然与一寡妇平起平坐?”
李侍郎面露难色:“此事毕竟是沈家家事,陛下都已准奏,我们如何插手?”
“如何不能插手?”李嫣然抬起泪眼,眼中闪过一丝狠决,“爹是礼部侍郎,最重礼法纲常!肩祧两房本就易生弊端,混淆宗法!沈家此举,看似全了孝义,实则后患无穷!爹只需在朝中稍作议论,自然会有御史言官跟进。再说……”
她语气稍顿,压低了声音,带着蛊惑:“沈聿如今圣眷正浓,又刚立战功,是多少人想拉拢的对象?若是让他兼祧长房,娶了沈弄月,那长房一脉的资源人脉岂不尽归他手?届时他权势更盛,对东宫……可是好事?”她巧妙地将此事与朝堂党争联系了起来。
李侍郎神色一动,显然被说中了心事。他确实是太子一党。
李嫣然见父亲意动,再加一把火,哭得更加哀婉凄楚:“女儿此生只愿嫁与沈聿,若不能如愿,宁愿绞了头发做姑子去!爹娘就忍心看女儿终身无靠吗?”她深知父母对自己的宠爱,尤其是母亲,几乎对她百依百顺。
李夫人果然急了,连忙对丈夫道:“老爷!我们就嫣然这么一个嫡出的宝贝女儿,她的心愿无论如何也得成全了!那沈家不过是要延续香火,让沈聿娶了嫣然,日后多纳几房妾室,生了孩子过继一个给长房不就是了?何必非要娶那个寡妇,委屈我们嫣然!”
“胡闹!靖远侯的婚事,岂是你说如何就如何的?”李侍郎斥道,但语气已不似方才坚决。
李嫣然见状,知道火候已到,她缓缓跪下,仰着脸,泪珠儿滚落,语气却异常坚定:“爹,娘,女儿并非不知轻重。女儿心悦靖远侯,并非为一己私情。若能嫁入侯府,于父亲、于太子殿下,岂非也是一大助益?女儿定会相夫教子,助侯爷稳固权势,绝不会让爹娘失望。求爹娘成全!”
她一番话,既表了深情,又摆了利害,更是下了保证。
李侍郎看着跪在地上、哭得如带雨海棠般的女儿,终究是长长叹了口气。他何尝不想与如日中天的靖远侯联姻?只是原先顾忌沈聿态度不明,才未贸然提亲。如今被女儿这般逼迫,又觉她所言确有几分道理。
“罢了罢了,你起来吧。”李侍郎挥挥手,“此事……容我仔细斟酌,寻机探探沈家口风。”
李嫣然心中大喜,知道父亲这是答应了。她乖巧地起身,擦干眼泪,又恢复了那副温婉柔顺的模样:“多谢爹娘。女儿相信,以爹爹的手段,定然能成全女儿。”
只是低垂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势在必得的锐光。
苏弄月?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也配和她争?
既然沈家动了这个念头,那就别怪她先下手为强了。无论如何,靖远侯夫人的位置,只能是她的!谁敢挡路,就别怪她心狠手辣!
她仿佛已经看到,那个如兰花般清雅的女人,是如何在她的手段下,悄无声息地凋零枯萎。
而此刻的兰馨苑内,弄月正仔细修剪着一盆兰草的枯叶,阳光落在她沉静的侧脸上。
她不知风暴正在酝酿,但那个预知的梦境,已让她心生警惕。她轻轻抚过柔嫩的花瓣,低语呢喃,仿佛在对自己说:
“风雨欲来……但我不会再任人采撷,零落成泥了。”
宅斗文里大嫂3
沈聿从兰馨苑回来后,心中那丝若有似无的波澜尚未完全平复,便被请到了沈老夫人的福寿堂。
堂内檀香袅袅,沈老夫人并未如往常般捻着佛珠,只是静静坐在上首,面前摆着两盏刚沏好的君山银针。
“母亲。”沈聿行礼后坐下,神色已恢复一贯的沉稳冷峻。
老夫人并未立刻开口,只是细细打量着自己这个出色的次子。他眉眼间与惟清相似,气质却截然不同,更深沉,更难以捉摸。她轻轻叹了口气,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聿儿,三日已过,你考虑得如何了?”
沈聿端起茶盏,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眼底的神色:“母亲,此事关乎重大,并非儿戏。大嫂年轻守寡,令人扼腕,但以肩祧之名行娶嫂之实,于礼法……”
“礼法?”老夫人轻轻打断他,目光如炬,“沈家满门忠烈,你父兄皆为国捐躯,陛下体恤,特旨恩准,这便是最大的礼法!长房不能绝后,这是沈家的根脉,比什么都重要!”
她语气转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惟清走了,我这心里……跟刀割一样。你大哥他……连个后都没留下啊……”提及长子,老夫人眼眶微红,声音哽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