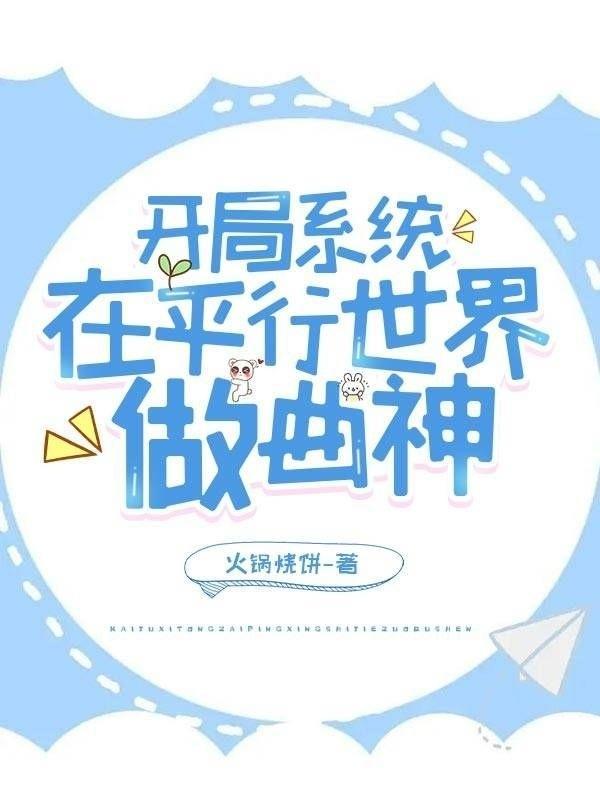富士小说>皇城有好事by清闲丫头免费阅读 > 第 98 章(第3页)
第 98 章(第3页)
甚至现在,光天朗日之下,他还想如此,想把她拥入怀中,想亲吻她。
不为疼惜,不为怜悯,也不为赏识,却又与这些全都有关。
是因为这个人。
她的一切。
庄和初再如何擅于自控,也非生来如此,就如他身上其他的本事,都是从无到有日复一日训练,以及从无数次吃亏受挫中磨砺而来。
是以他对此也算颇有经验。
在某一事上不可自控,最简单有效的法子,便是从根源断绝。
譬如,不能见光的,就要尽快将它曝于光天化日下。
“千钟,还有件事,我要与你说句实话。昨夜——”庄和初一下决心就断然开口,可话已出口,又怕一下子说到头,会吓坏了她,还是略缓了一缓,先道,“昨夜,我抱了你。”
昨夜?
她趁他睡着偷偷摸他,被他在睡梦中一把搂住,那不是前天夜里的事吗?
千钟一愣,差点儿脱口问出来,忽然及时反应过来,自己要提起这茬,岂不是不打自招了?
“那……”千钟心头一转,“那肯定是我睡觉不老实,先碍着您啦。”
“我还亲了你。”庄和初自顾自道。
“亲我?”千钟一愣,怔怔地看着他,目光里的茫然之色与方才无法领会写字要点时如出一辙,“亲我……是什麽意思?”
庄和初被问得一噎。
也对。
街上人说风月之事,并不会讲起这些细节,更没有人在街上做这种事。谢恂那时以落魄书生自居,连周公之礼都未曾与她讲过,这些就更不会了。
“就是……”
庄和初将自己方才为她纠正握笔的那只手擡起靠到唇边,在手指边缘上轻轻吻了一下。
“这样,碰了你。”
千钟眉头一拧,垂下目光,好像在思量些什麽。
庄和初不愿去猜她思量的结果。
“今夜——”庄和初刚要说,今夜起,他会睡回外间,不会再与她同榻,才一开口,就听千钟忽道了声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这事,我见过。”千钟亮闪闪地眨着眼,向他求教似地道,“我在街上看见过,有些爹娘就把他们的孩子抱起来,在他们脸颊上啄一下。那样就叫……亲,对吗?”
庄和初一时有些啼笑皆非,到底点头,“那样……也算。”
千钟不知道被亲一下是什麽滋味,但她清楚地瞧见,那些小孩子和他们爹娘都是高兴的,照她看,这该不是什麽坏事。
可瞧着庄和初的神情,听着他话间的口气,又好像并非如此。
“这样,不好吗?”千钟不解道。
对着一张无瑕白纸,便是笔力再精到之人,也不敢轻易落笔。
可十七楼如此浩繁的藏书里,也没有那一卷能清楚明白地讲通这些。没有先贤教诲在前,只有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最切实的感受。
“不得人准许,不可以,是罪过。”庄和初又慎重注解道,“或许,你知道何为冒犯丶轻薄丶玷污,大概就是这类的意思。”
这麽听着,好像是个不小的罪名。
他那好似有意避着她的古怪之举,也是因为这个?
千钟定定望着那罪人,望着望着,忽一踮脚凑上前,在那片血色淡白的脸颊上飞快地啄了一下。
而後大退一步,又一步。
“这样,我也玷污您了,咱们就算扯平了吧。”
千钟抿抿唇,忽闪着一双眼睛小心觑着那被她亲得呆愣原地的人,心里一阵阵打着鼓,嘴上壮着胆子讨价还价。
“我饶了您,您也饶过我,行不行?”
亲吻她,和被她亲吻,完全不是一回事。
何况,他是在床帐中如墨夜色下,她是在光天化日下,是在这……
先贤着述盈满四壁,桌案上是应时的水仙清供,玉台金盏,清雅幽冽,窗下插瓶的是松枝丶竹枝与梅枝,岁寒三友,高洁磊落。
窗台上不知何时还蹲了一排晒太阳的雀鸟……
本该是明心见性之地。
千钟只见那人眸光凝在她脸上,似有火光跃动,可到底只微微啓齿,如水般清淡地道了一句不行。
“啊?”千钟正想再往远挪,又听那人接着道。
“我亲了你两下,”庄和初面不改色道,“你只亲一下,扯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