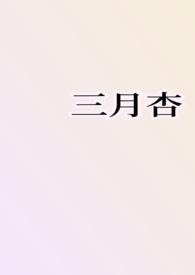富士小说>古代养家日常免费阅读无防盗章节 > 第104章(第1页)
第104章(第1页)
急匆匆回到驿站,沈元惜已经换了身干净的一群,半躺在床上,身下拿旧衣物垫着,裙摆只遮到膝盖,两条白皙瘦弱的小腿就这么大剌剌的露在外面。
谢惜朝差点以为自己刚刚没敲门,可他分明是听到沈元惜说进来的时候才推开门的。
少年一瞬间变得面红耳赤,狼狈的丢下布包就摔门离去。
当了二十几年现代人的沈元惜没反应过来自己又戳到了他哪根脆弱的神经,扶着腰站起身去捡那个布包,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动作,就被小腹剧烈的坠痛折磨的冷汗涔涔。
等她终于收拾好,能勉强起身走两步,刚拉开门准备出去寻谢惜朝,正撞上拎着热茶壶进来的谢惜朝。
“怎么起来了?我给你煮了红糖姜水,喝了应该能好些。”谢惜朝忙将人推了回去,拾起扣在桌面上的水盏倒满滚烫的姜糖水,等到稍微凉些才端起来递给沈元惜。
看着他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样子,沈元惜一乐,冰凉的手也被这一碗姜糖水暖得热了些。
谢惜朝放得糖不少,因此味道还可以,沈元惜一连喝了两碗,腹痛缓解了许多,效果立竿见影。
可见这副身体不是痛经体质,之所以难受,全怪沈元惜不注意,喝多了凉茶。
不幸中的万幸,沈元惜松了一口气。
打法走了谢惜朝,她将被血染过的衣服团成团放在了角落,这么好的衣料只穿过几次,扔了怪可惜的,血迹洗不掉便裁了做其他的,总之不要浪费。
眼下状况也不适合赶路,于是沈元惜也不得不耐下性子在驿站多住几日,顺便处理了尉迟氏这个大麻烦。
吐谷浑那位小公主有门路,将两万金兑成了盖了大历官印的钱票,沈元惜拿到手也就一个小木匣子,掂在手里不算沉,远不如真真切切拿在手里的金子有分量。
就这一个不大的盒子,里面码的整整齐齐,跟一包碰上了暴力快递的a4打印纸似的,皱巴巴的厚厚一摞。
谢惜朝在拨往各地的军费赈灾款以外,就没见过这么多钱,看着沈元惜三下五除二的清点完,有些瞠目结舌。
那可是两万黄金,相当于二十万两银,两万万文钱,即便是东洲那次那么大规模的地动,朝廷也不过送了四十万两银的赈灾款过去。
这一个尉迟王姬就能从吐谷浑小公主手中捞出来二分之一,看来这些年没少背地里从大历谋财。
其实不止背地里,大历自今上即位,向来主和不主战,诸国来犯,只要不至于到割地的程度,往往都是以和亲公主的嫁妆的名义奉上大把金银财帛,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如今西北诸国,已经有好几位王后出自大历,全都是谢惜朝的姑母姊妹。
皇宫中的几位公主,除了那二位最尊贵的,其余都是稚童的年纪便已算计好了归宿。
沈元惜初来乍到不明内情,但谢惜朝却清楚的很,他的父皇为了一个仁德的名声,几乎快要将如今的大历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
这一点,无论是谢琅还是谢惜朝,都不能容忍。
因此,争斗的你死我活的二人只有在这方面,才能短暂的达成和解。
他们都盯着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一旦他稍微透露出一点要削减军队的意思,那么谢惜朝哪怕拼个弑君弑父的罪名,也会要了他的命。
他与那人,是君臣、是仇人,却唯独不是父子。
好在景帝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没做出亲手除去大历利刃之事。
谢惜朝出神这片刻功夫,沈元惜已经攥着钱票在数第二遍了。
沈元惜觉得自己就是个点钞机,穿到古代来,数珍珠、数金砖、数银票,几乎每一次都数额巨大,还不能有一点疏漏。
她这般想着,嘴也不自觉的秃噜了出来。
谢惜朝闻言,好奇道:“点钞机是什么?”
钞票他晓得,沈元惜说过,与银票类似,几乎已经代替了金银,成为主流,至于为什么是几乎。
当然是电子支付已经占领全大陆,年轻人哪个没有蚂蚁花呗,就连沈元惜也在余额宝上存了一笔不小的数目,每天收着仨瓜俩枣的利息,节俭度日。
倒霉催的,大笔存款没来得及花,甚至房贷都还没有还完,沈元惜就穿到了这没有暖电燃气的古代,水还得自己从井里挑。
谢惜朝一句话戳到了她痛处,悲伤顿时水漫金山似的淹没了沈元惜,哪里还有兴致回答他的问题?
沈元惜烦躁,重重将银票往桌上一拍,开始撵人:“我累了,你出去吧。”
谢惜朝看着窗子外面正当空的烈日,疑惑几乎要从脸上溢出来。
“我的一千多万存款,还没来得及花!”沈元惜一脸生无可恋。
谢惜朝吓了一跳:“这么多?”
他对现代的钱没有概念,骤听到一千万那么大的数字,惊异不已。
按照沈元惜所说,她以前是在洋人手底下打工的,能攒下这么多钱实属不易,还没来得及挥霍就一命呜呼,真是惨绝人寰。
沈元惜只是嚎一嗓子,并没有意识到谢惜朝思维这么发散。
毕竟真算起来,她在现代年薪再高,也只是个打工的,穿到大历这短短一年赚的钱,换算成钞票,她一辈子工资加起来都不够。
当然,宁做现代一条社畜,也不做古代贵族。
千年间时代的进步,哪怕是最普通的朝九晚六的工薪族,生活水平不说比皇帝,至少也吊打朝中大员。
还是除了三餐以外全方位的那种。
无论是空调暖气热水器,还是电梯地铁公交车,都是古人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