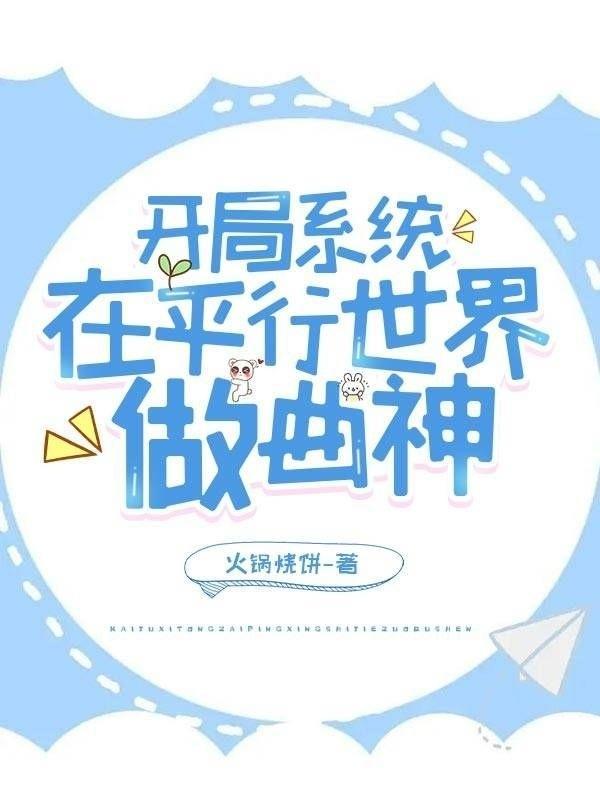富士小说>叶落是什么 > 第 11 章(第1页)
第 11 章(第1页)
第11章
青石巷的石榴树影在叶聿炀左手笨拙的线条下,扭曲成一个比例失调丶枝叶团簇的怪异轮廓。
阳光灼烤着青石板,也蒸腾着他额角细密的汗珠。左手食指和中指因为长时间用力握笔,关节处已经磨得发红发痛,微微颤抖。
巷子里偶尔有街坊路过,投来好奇或善意的目光,王阿婆甚至从院子里探出头,笑眯眯地喊了句:“慢慢画,不急!阿婆给你留熟透的石榴!”
叶聿炀没有擡头,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左手那支不驯服的炭笔和眼前那棵生机勃勃的石榴树之间巨大的鸿沟上。观察,落笔;再观察,再落笔。
每一次重复,都让他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左手的笨拙和技巧的匮乏。那些曾经如同呼吸般自然的构图丶透视丶光影处理,此刻如同遗失在遥远彼岸的珍宝,遥不可及。
但他没有停下。
没有像以前那样暴怒地撕碎画纸。
一种近乎自虐的丶或者说是一种向自身局限发起挑战的倔强,支撑着他。他不再是那个不容瑕疵的天才,而是一个挣扎着丶用残缺的工具重新学习表达方式的学徒。
每一根歪斜的线条,每一个比例失调的结构,都像一枚笨拙的脚印,记录着他在这条荆棘小路上的跋涉。
直到左手酸痛得再也握不住笔,他才颓然地停下。速写本上那棵“石榴树”,与其说是树,不如说是一团混乱的丶带着挣扎痕迹的墨迹。
他合上本子,靠在微热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右臂经过上午的艾灸和推拿,温热松弛的感觉依旧清晰,手腕处的僵硬感确实减轻了不少,这微小的进步是支撑他此刻没有彻底崩溃的唯一慰藉。
下午,叶聿炀再次走进回春堂时,脚步比往日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沉重。
推拿按压带来的酸胀麻痛依旧强烈,但这一次,他咬紧牙关忍耐时,脑海里不再是纯粹的痛苦,而是交替闪现着那棵真实的石榴树和自己纸上那团扭曲的墨迹。
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在他脑海中碰撞,带来一种奇异的焦灼感。
当艾灸盒温暖的烟雾再次包裹住他的手腕时,那深入骨髓的舒适感稍稍抚平了内心的烦躁。
他靠在隔间的单人床上,闭着眼,感受着艾火的温热顺着筋络缓缓流淌。
隔间外,隐约传来炭笔在纸上摩擦的沙沙声——林青竹又在画画。
那声音很轻,很规律,带着一种全神贯注的韵律感。
叶聿炀的耳朵不由自主地捕捉着这细微的声响。这声音不同于他左手画时那种滞涩丶挣扎的沙沙声,它更流畅,更自信,虽然技巧同样稚嫩,却透着一种纯粹沉浸其中的安然。
他仿佛能看到她低垂的眉眼,微微抿起的唇,和那支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的炭笔。
治疗结束,右臂温热依旧。他擦掉药油,走出隔间。
林青竹果然还在诊桌旁,不过这次没有画插花的陶罐。她面前摊开着那本深蓝色速写本,手里拿着炭笔,微微蹙着眉,似乎在为什麽难题困扰。
画纸上,是几株形态复杂的蕨类植物,叶片层层叠叠,姿态舒展,显然是她今天采药带回来的新“模特”。
叶聿炀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画稿上。能看出她试图捕捉蕨叶那种特有的丶如同羽毛般轻盈又繁复的姿态,但线条在描绘叶片的细节和整体舒展感时,明显出现了犹豫和混乱,画面显得有些局促和呆板。
林青竹似乎感觉到了目光,擡起头。清澈的眼眸里带着一丝被打断思路的茫然,随即恢复了平静。
她没有像上次那样立刻合上画册,只是将目光重新投向桌上的蕨类植物,眉宇间那点困扰依旧清晰。
叶聿炀的脚步顿住了。
他看着那几株生机勃勃的蕨类植物,又看看林青竹画稿上略显僵硬的线条。
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脑海,快得让他自己都措手不及。那棵石榴树扭曲的轮廓和眼前蕨类植物僵硬的线条,在他脑海中産生了某种奇异的共鸣——都是因为无法准确捕捉对象的神韵和动态。
几乎是脱口而出,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安静的诊室里响起:
“叶脉……主脉和支脉的交汇点……力量感……”声音不大,带着迟疑和久未进行专业交流的生涩。
林青竹握着炭笔的手猛地顿住。
她倏地擡起头,清澈的眼眸第一次带着清晰的惊讶,直直地看向叶聿炀。那目光不再平静无波,而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探究,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