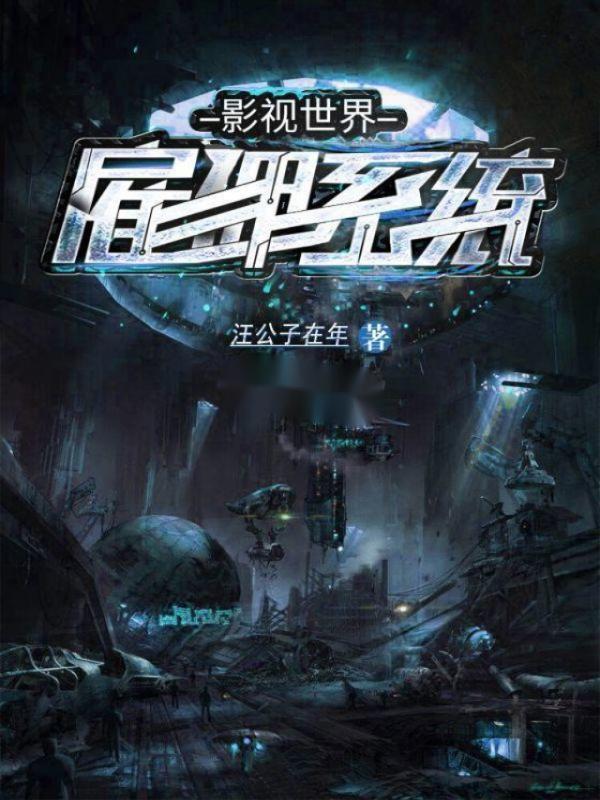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死过一次才明白 > Chapter丶45 重啓(第5页)
Chapter丶45 重啓(第5页)
我找到了闻瑕跳下去的那个二楼。
房子主人收拾过现场,只是不经心,一层外围拐角的花盆挪开,里面有浸入墙体的棕黑痕迹,是干涸的丶被闻瑕疼到呕出来的血。
搬回花盆时发现湿漉漉的,我低头,才发现手心全是深深的丶不知觉掐出血的指甲印。
我并没有自述中的这麽镇定。我视线一点点爬过簇簇草木,一寸寸恨视着这座吞噬了闻瑕生命的房屋。这里面住着的是谁?真的是柳白楠麽?
我仔细擦干净花盆边缘沾染的血迹,模糊掉脚印,心里却在此刻总不断冒出极悚然荒唐的想法——这房子里面住的人,不像是柳白楠。
柳白楠年纪轻轻已是知名导演,命运一帆风顺,所以他张扬丶肆意丶不计後果,更要面子,他始终是新潮派,坚持自己引领风尚,所以他永远不会选择这个十几年前就建造出的豪宅,哪怕这曾是这个城市最顶级的。
它已经在某些角度泛起老化腐旧的黄边,有土和泥的味道,我在低处向上望,它就在高处冲我亮起凶狠又自得的爪牙。人在最接近真相时最疯狂,也最不要命。几乎没有多馀的思考,我顺着浓黑厚重的夜色,从下往上爬上了这个闻瑕姐由上落下的痛苦开端。
呜——
急促刺耳的警报声,甚至短短几分钟远处便开始有红蓝光交替闪烁,嘀呜嘀呜嘀呜之声不绝。
红蓝光照的人心安,我还有心思笑笑。
借着光,我看清了客厅里相框中的照片——那是一个温润清和的丶令人感到眼熟的中年男人。
我不认识他,却觉得见过他,等了两秒,搜索软件的识图结果显示,他是吴尚璋。
哪个吴尚璋?
我向下刷了下百科界面,一指到不了头。
……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耗费近十年的布局让这孩子找到了突破口,不,或许称之为‘火种’,更合适。”关婉玉收起看向信的视线,瞥了眼傅岐始终放在身边近处的铝饭盒。其实关女士的这一眼并没什麽特别的意思,但傅岐就是警惕地丶下意识地挡住了饭盒。
“藏什麽?我还能抢你的东西?”关婉玉一脸的心平气和:“还有什麽,都拿出来吧?”
第三封,第四封,展开,放整齐。
“……这孩子”
关婉玉笑了一声,有些无奈:“偷着跟你骂我呢。”
傅岐唇锋紧紧抿着,一直到听到这句话,他才在微微怔愣之後,短暂又几不可闻地笑了下。
第五封,在少许犹豫後拿了出来,傅岐解释道:“这个不是给我的,你看,小俞是这样写我名字的。”
他手指沾了点茶水,写在茶桌上:“这样,和我一样,我教会他的。”
“你还挺骄傲”,关女士睨他一眼,擡手把茶倒了:“你说不是写给你的,那怎麽他那把刀又冲着你去了?”
“他没冲我”,傅岐摇头道:“他永远不可能冲我,我想,应该是有什麽改变了他的计划。”
“比如?”
“我。”
傅岐眷恋地扫向每一封信:“在哪死丶怎麽死丶因谁而死,其实都一样,意义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复仇。但在我这里不一样,他的死亡会换来我的决心丶我的执念,会让我不顾一切用尽全力把事情解决,他早就明白,我心里哪有什麽恨,哪有什麽埋怨,哄一哄,就好了。”
“得哄,认认真真的哄,不是故意伏低做小丶低声下气,那不是哄,那是气我”,傅岐偏了下头,好似真的是在对我说,但也只是捋着铝饭盒的边儿,把它摆的正了正,“笨蛋,气死我算了。”
“对不起”,我条件反射地。想了想,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那样很有诚意,对不起。”
静寂的几分钟里只剩水壶咕嘟咕嘟的冒泡声音,关女士沉静地看着他,少顷後:“你要解决什麽,傅岐?”
关婉玉揉揉眉心,像是突然明白了什麽,叹了口气:“明明跟你毫无干系。”
“那条牵起来的线,是个女孩子,叫张瑕,不过你应该知道了,那就是那孩子的亲姐姐。”
关婉玉停下,若有所思:“……你要不要来猜猜看,他们都做了些什麽?”
恶劣的问题。
傅岐看起来并不想回答,拒绝了。
关女士闭了闭眼,缓缓睁开:“低劣丶恶毒,毫不光彩,令人作呕。”
也让人痛苦。
我想,真相会让所有人感到痛苦。
“你说出‘解决’时,我知道你是怎麽想的,儿子。”然而,关女士话锋一转:“你在想你有的是钱,而这些钱也赋予了你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你得出结论,只要你奉上所有钱就是竭尽全力,就没什麽是解决不了的,真是这样麽?如此简单!傅岐,你以为我会甘愿舍出去那个孩子的性命?”
“钱只是加入他们的门票,不是瓦解他们的武器。”关婉玉冷冷道:“你得认识到,你那账户上长串的馀额不是万能的。”
“钱谁都有,但怎麽花丶能不能花丶谁来花,这是问题的根源。无论是沈广平还是吴尚璋,这麽多年的积累早就让他们实现了财富上的自由,但沈广平有亲生的女儿,有白得的儿子,吴尚璋有什麽?没有,他只能和吴尚邱平分一个孩子。”
“所以吴尚璋想要一个干净的漂亮孩子,沈广平的儿子就主动搭起来这条线。他大致是利用身份精神控制了许多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意图为吴尚璋生子。但事情远没有那麽简单,他吴尚璋是半个天阉,这事始终未能成功……可这一下却打通了沈广平儿子的任督二脉,他利用如此,拉拢了更多的人。”
无形的虚空像被什麽凝固住了,傅岐眼中交织困惑,下一秒是即刻的愤怒。
良久,傅岐才缓缓开口:“闻瑕的体检报告被小俞更换过几页,我当时猜……”
傅岐闭上了眼。
关婉玉看向他憔悴的神情,微微叹气:“你没猜错,他们做的就是强迫致孕,张瑕也逃不过。”
这句话说出来时,我的耳膜又开始嗡嗡作响起来,下意识退後了两步。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