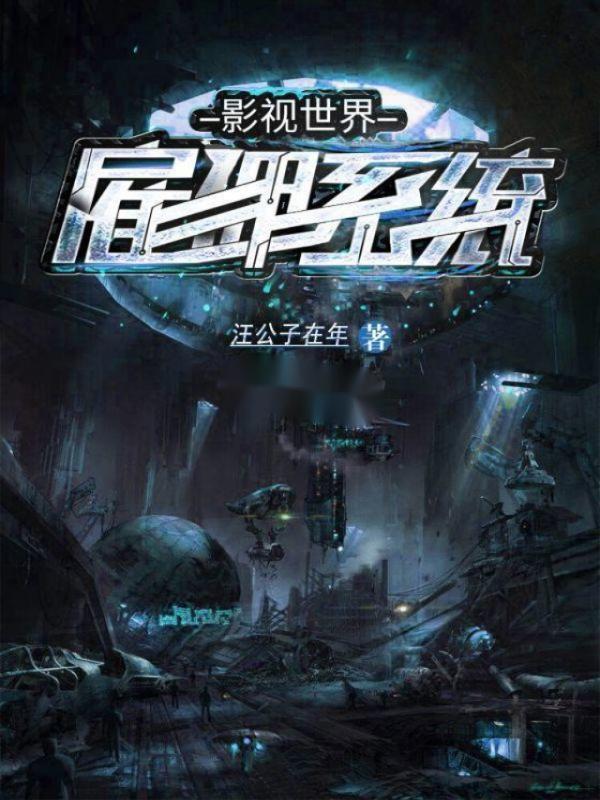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太子妃为何不侍寝 在线阅读 > 第295章 旧念不回(第1页)
第295章 旧念不回(第1页)
白隐走了,就同白隐细作身份被揭穿的那几日一样,江箐瑶闷闷不乐,不吃也不喝。
纵使江箐瑶有千斤重的骨气,纵然她很清楚这才是两人该有的结局,可在斩断情缘时,情感却是不受控的。
她一边骂着白隐,一边说他走得好,也一边庆幸自己终于不用再愧疚活着。
可她还是不争气地躲在屋里哭个不停。
江箐珂闲来无事,便同喜晴陪着她,时不时损江箐瑶几句,再同她贫几句。
可江箐瑶就好像心死了一般,都懒得跟江箐珂吵架。
她时常会盯着一处呆,眨眨眼,偶尔声色无力地同江箐珂说上一句。
“白隐总是坐在那儿陪翊安玩儿,早上阳光斜照进来,正好照着他们父子俩,看起来很是暖心。”
“他刚入府为奴时,我都是让他打地铺睡在那里的,下雨天,夜里又冷又潮的,他也不吭声。”
“墙上的那幅山水画,是白隐画的,有一次他同我说,那是他儿时与家人游玩时曾去过的地方。”
“喜晴坐的那个凳子之前坏过,是白隐修好的,他最喜欢鼓弄这些木头了,还说明年给我和翊安做个摇椅呢,结果”
小小的屋子,落在江箐瑶眼里,每一处都是回忆。
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都在这日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许是在一起的日子太久了,她说也说不完,连带着泪水也流个不停。
江箐珂也没了调侃嘲讽的劲儿,柔声劝她。
“吃点东西吧,至少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或许白隐哪天想你想得要紧,就回来了呢。”
江箐瑶揪着心口处的衣衫,神情痛苦地摇着头,泪水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他都能狠心留下书信离开,且从年前就开始准备,定是下了决心的。”
“阿姐,我这里好难受啊,感觉要憋死了。”
“你说我为何这般没用,竟对个杀父仇人念念不忘,爱死爱活的。”
江箐珂都不敢告诉江箐瑶实情。
若她知晓白隐去西燕当细作,未来生死难料,还不知江箐瑶得担心、难过成什么样子。
左右也是该忘记的人和事,不说也罢。
江箐珂声色平平,只能劝她多想想孩子。
“你还有翊安,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江箐瑶一脸颓然,转身躺下,蒙着被子在里面哭。
想起自己跟李玄尧分离时,也像江箐瑶这样哭得死去活来的,江箐珂感同身受。
她不由想起尚在北燕的江昱曾说过的那句话。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动了心的女子想走出儿女情长的困顿,怕是要活活扒层皮才行。
最糟糕的是,明明只是相伴了一阵子,人走了,却要想念一辈子。
江箐珂本是没那么赞同李玄尧的解法,可瞧着眼下这番情形,觉得那法子也不错。
干净利落,少了许多痛苦。
起身回房,她同李玄尧点了头,找来张氏细说了一番,张氏听后倒是巴不得的。
见状,李玄尧抬手打了个指响,同曹公公示意。
翌日,一切准备就绪。
江箐珂带人进了江箐瑶的屋子里。
白隐每日摆弄木头的那处,江箐瑶顶着红肿的双眼,神色憔悴地坐在那里,手里是一个木雕人偶。
“阿姐。”
江箐瑶抬眼看向她,恹恹道:“怎么办啊?白隐一直在我眼前转,赶都赶不走。”
“你说他到底会不会回来了?”
“为何都不跟我说一声,留封信就走了呢?”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