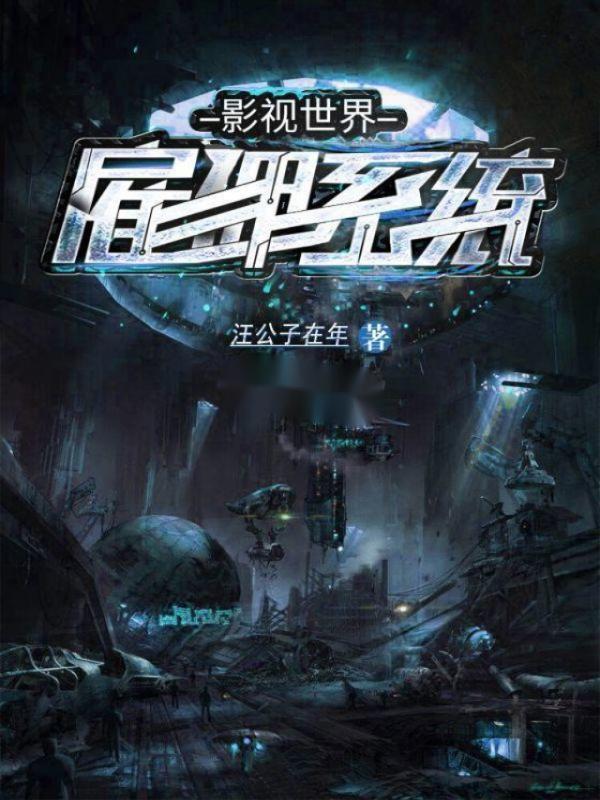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宿敌看我的眼神逐渐变质漫画下拉 > 59(第1页)
59(第1页)
59
天亮,阳光明媚。
吃过早饭,白桐和白浔去扫墓。
叶衡的墓地在城郊。汽车驶出柏油路,还要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走一段。
经过一座水泥桥,白浔问:“阿姨,这条渠是什麽时候修的?”
“五年前。”白桐说,“为了方便灌溉农田,政府弃用了自然渠,在原址上新建了这条渠。”
渠水约两米深,前方一百米处有一道闸口,汹涌的水流遇到阻拦,冲撞出雪白的浪花。水势很大,声音震耳。
“前两天接连下雨,水涨得好高,怪瘆人的。”白桐想起一件事,“那个男人死了,尸体就是从这条渠里打捞上来的。”
白浔心知白桐说的是谁:“意外落水?还是被人抛尸?”
“警方通报的是醉酒後失足落水。”白桐忽然明白叶然为什麽发火了。前年五月,叶然的确回了家。男人的死讯,还是她告诉她的。
二号早上,母女俩给叶衡扫墓。
下午,叶然出了门,说随便转转。
傍晚下了场瓢泼大雨,叶然浑身湿透着回来,把自己锁进卫生间泡澡,出来的时候鼻青脸肿。白桐问怎麽搞的?叶然没有吭声,连晚饭都不吃,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饭桌上,叶然举着手机给白桐看,官方通报,渠中打捞出一具男尸。
当时,白桐恶狠狠咒骂:“罪有应得!”叶然却说:“便宜他了!应该把他活剐了才解气。”她说话时咬牙切齿,表情从未有过的狠鸷,看得白桐心里犯怵。
叶衡的墓地周围有几十棵罗汉松,是她下葬後白桐种的,七年时间,小树苗已经长大,枝叶翠意盎然。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献上鲜花和瓜果,火苗燃起,冥币在高温中弓起脊背,蜷成一个个颤抖的弧。
烟气袅袅升腾,白浔的心头浮现出她和叶衡相处的点滴。
出车祸的那天,似乎冥冥之中有预感,叶衡给她打电话。
“阿浔,我有点想你。”叶衡说,“我想起你小时候的样子,调皮捣蛋得不得了,翻墙爬树,打弹弓丶滚铁环,总是玩得灰头土脸,简直是个假小子。”
那天是周六,白浔着急去兼职,没有功夫陪着叶衡回忆往昔:“妈,我先去忙,晚上回来聊。”
叶衡叹了一口气,白浔感到一阵燥热,仿佛母亲就在身旁,她吐出的那口气,刚好吹过她的脸颊。
“你从小就独立勇敢有主见,是个好孩子。”叶衡说,“能做你的母亲,我觉得十分幸运。”
白浔顿住脚步,刹那间,她对叶衡的不满荡然无存,像汹涌的海浪冲刷过沙滩,把一切污垢荡涤得干干净净。
她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妈,您认为我是个好孩子?”
“当然了。我以你为荣。”叶衡好像也在哭,鼻音很重。
公交到站,白浔老泪纵横地跳上车,在司机困惑的眼神中刷卡,嘀——两元。
“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身体,吃饱睡好,别太拼。”叶衡说,“咱们晚上再聊。”
然而,生命之于叶衡,已经不再具有夜晚。那是两人的最後一通电话,白浔兼职结束,回学校的路上,看到一条短信,八个字,叶衡说——好好活着,妈妈爱你!发送时间是半小时前。
白浔正纳闷今天的叶衡十分反常,就接到白桐的电话——叶衡出了车祸,还没有来得及送往医院,已经断气。
短信,应该是她昏迷前发的。
望着叶衡的遗像,白浔心中酸楚。所谓缘分一场,只是短暂相逢,漫长煎熬,骤然间生死相隔,到头来,许多事,了而未了,终以不了了之。
因为叶衡的遗嘱,日子即便再难熬,白浔都没有选择轻生——她要活着!活给命运看,她是怎样在它的暴击中站起来,又怎样昂首挺胸地走下去!
墓碑上的刻字清晰如初。白桐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加深墨记,到死,她给叶衡安上了“挚爱”的身份。
两人相识于年少,也曾情意缱绻,只是,浓情蜜意终究被岁月消磨,海誓山盟土崩瓦解,深藏于心底的怨恨就分外扎眼。
那年,二十出头的白桐去参加舞蹈比赛,风华正茂,兴致昂扬。拐角处,叶衡骑车而来,刹车失灵,横冲直撞。
自行车碾断了白桐的腿,她落下病根,自此不能登台,梦想破碎,不甘又无奈地回到家乡。叶衡极有担当地辞掉了大城市的优渥工作,陪着白桐从头开始。
两人做过许多营生,八九十年代,抓住风口做生意,积攒起家业。
三十岁,叶衡想做母亲,两人几番波折,意外地带来一对姐妹花。
她们用对方的姓,给自己的孩子做姓,以此来纪念这份讳莫如深的感情。然後,把对对方的爱,贯注在对方的孩子身上,又把对对方的埋怨,移情到和对方同姓的孩子身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看着墓碑,白桐无限感伤。活得比叶衡久,像是一种惩罚。这些年,悔恨丶遗憾丶无聊丶空虚。。。。。。将她围得密不透风。
如果来生还能遇见,希望我们相敬如宾过一生。白桐这样想着,掏出手绢,擦一擦叶衡遗像上的灰尘。
纸页在烟火里扑腾,最终化为零落的残星。灰烬随风扬起,转眼消失于无痕。
*
另一边,大清早,微薄“小炸”。
狗仔扬言明天曝光栗粒的新恋情,乔峤在“驻凡大使群”呼号:【粒宝,怎麽回事?】
栗粒毫不避讳,把狗仔要发的内容发到群里,是她和叶然在ME大厦门口的互动,一段十秒的视频,是她们的拥抱和耳语,五张是见面和告别时的拥抱照,为了对比,还附带栗粒与白浔和宋焘的握手图。
栗粒:【他要我花钱买断,否则就发稿。】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