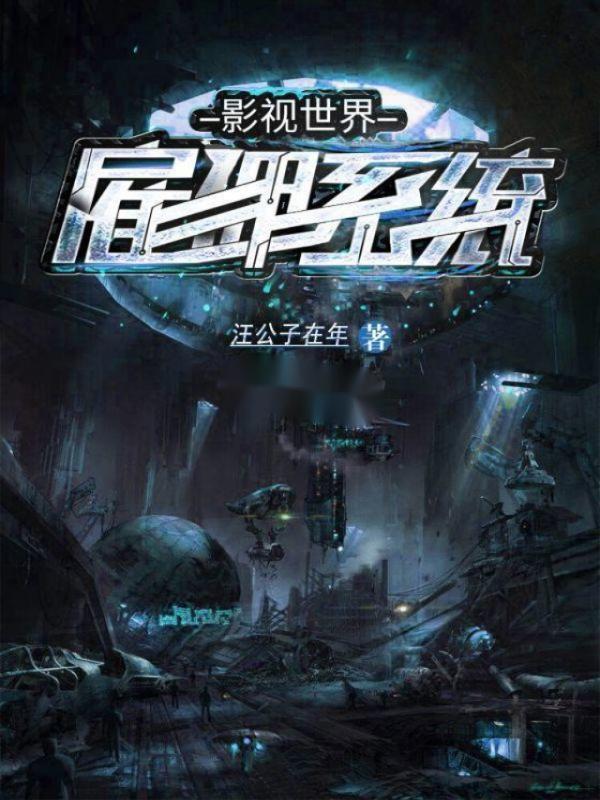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万人嫌的攻略手册穿书 > 中止(第1页)
中止(第1页)
中止
迟糖以为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他的身体非常滚烫,喉咙也干哑,腿也很疼,动一下就疼的颤抖。
在长久的等待和疼痛中,以及害怕被人抓住的不安情绪,迟糖只能睁眼,逼自己打起精神,握匕首握了太久,手柄在他手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当面前的大石头推开时,阳光洒满了小小洞xue,迟糖以为是坏人来了,本能地挥动手里的匕首,看清了谁,瞬间僵住,匕首落在地面。
迟糖呆呆望着温珩景,麻木的眼睛逐渐变得微红。
温珩景胸腔起伏不平,跪下来紧紧抱住他,“没事了,糖糖,没事了,那些人都被抓起来了。”
他滚烫的呼吸落在自己的耳朵上,迟糖咬住唇瓣,呜咽了几声,开口就是哭腔,“我…我一直在等你,我以为我要死了。”
“对不起,是我来晚了,”温珩景心疼地亲吻他的额头,将他打横抱起,飞快朝救护车走,“不会死的,别怕。”
“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迟糖流着泪,他和温珩景最後一次见面,却是不欢而散的冷战,在知道自己有可能会死的时候,迟糖是很後悔的,“……对不起。”
温珩景稳稳地抱着他,“我们之後再说,糖糖,你在发烧。”
迟糖看着温珩景被刮伤的脸,伸出手碰了碰,意识逐渐不清醒,温珩景的脸在他眼中越来越模糊。
最後,彻底失去了意识。
其他人也发现了他们,看着温珩景抱着迟糖走来,顿时一拥而上。
“担架!!”
“杨医生!找到迟先生了!”
“让我看看迟糖!”
……
场面看似混乱,实则有条不紊,温珩景将在场的所有人都带走了,并留下人清场。
来了十几架私人飞机,防止出意外,有几架是专门引开人的。
至于温珩景会坐在哪一架没有人会知道。
飞机一落地,迟糖就住进了医院,重新清洗了身体并包扎了伤口,之前杨蕴只是固定了骨折的位置,没有打石膏,来了医院,全部重新做了一次。
中途迟糖疼醒了两次,打了麻醉又重新晕了。
幸好迟糖晕了,不然他也受不了这个疼,他对痛觉很敏感。
他睡了很久,是在凌晨三点饿醒的。
掀起沉重的眼皮,入目是白花花的天花板,他还没反应过来,手就被人用力握紧了。
“醒了,糖糖。”
迟糖的眼珠子缓慢转动,看见憔悴的温珩景,他的大脑正在逐渐复苏,恍惚的眼神也逐渐清明。
“景景……是在医院吗?”
温珩景坐在床边看他,“嗯,现在感觉怎麽样?疼吗?”
“嗯……”迟糖慢慢点头,“腿好像动不了。”
“骨折了,打了石膏。”
“左腿?”他之前觉得左腿更疼,右腿没有那麽疼。
温珩景拂过他眼睛上的头发,“不是,是两只腿。”
迟糖:……
他无奈地伸出手挣扎了下,发现自己起不来,两条腿都被吊了起来,不得不求助温珩景。
温珩景静静看他,没有动作,看似平静的脸上,蕴藏着波涛汹涌。
迟糖心虚地缩了缩手,“景景……我已经没事了啊。”
“不会再有下次了”,温珩景的语气没有起伏,调整了病床,扶着迟糖的腰部让他起来,“再有下次,就把你关起来。”
迟糖抖了下,瑟缩低着头,看着被扎成的手指,无措地在被子上抓了抓。
温珩景按了按墙上的按钮,让人送餐来,刚刚他听见迟糖肚子叫了。
饭菜很快就送来,夏良蜀推着餐车进来,他察觉病房内压抑严肃的气氛,默默地放下餐车赶紧离开了。
迟糖低着头,不敢看温珩景,不仅是因为自己自作主张冒险行事,更是因为他现在有点害怕温珩景。
他让温珩景生气了。
“擡头,张嘴,”温珩景拿起粥,吹了吹喂到迟糖嘴边。
迟糖默默张开了嘴,去喝粥,山药粥,很香。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