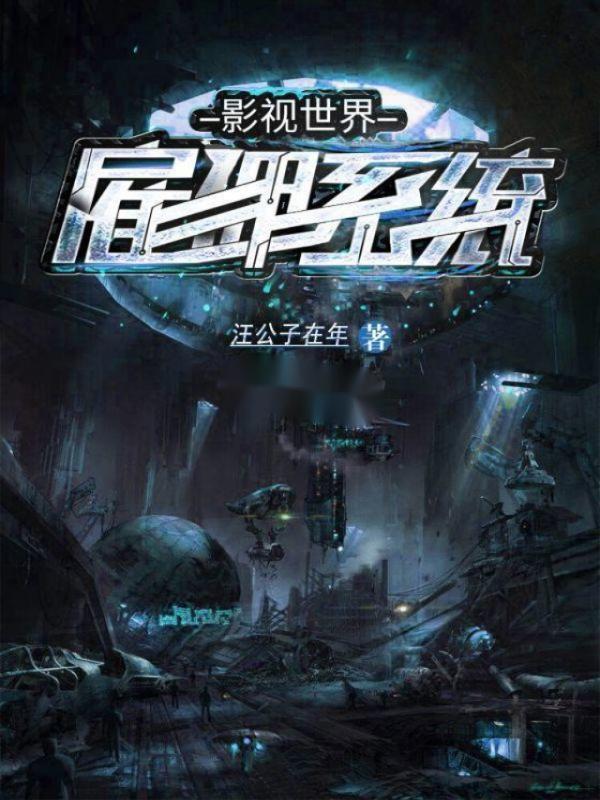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来一个儿科医生 > 探访猪场(第2页)
探访猪场(第2页)
越过堤坝,一阵排泄物臭气,乘着江风扑面而来。
看起来这宰猪场还兼养猪的。
“要不你在这儿等等我,走近了味道很大。”穆槐青才意识到,摸着脖子不好意思道。
周传钰半下半下地呼吸,循着风的方向伸脖子,看见了土砖围墙,“还没到忍不了的程度。就是那边吧?走吧。”
土砖头圈成的场子,蓝漆铁门只有半截,油漆也老化剥落。
“有人吗——”
穆槐青从半截子门上探身,拉长尾音喊。
“诶!”一上了年纪的女人跑来,手里还牵着正滴水的塑胶水管。
“是来买猪肉还是抓猪啊?”看是两个年轻姑娘,其中一个穿着还挺讲究,开了门便嘱咐,“正不巧在冲地,又脏又滑的,小心小心!”
穆槐青正往里走,闻言一顿,脚下站定,就在门口询问了起来。
“怎麽这麽早开始冲地了,杀猪生意这麽早就停吗?”穆槐青走进去询问。周传钰趁此往外退两步——门开了才看清地上到处是血水坑,被冲地水稀释过,粉的红的,像从地缝里洇出来似的,看着渗人。
“嗐呀,”老板把手往後边猪圈里一挥,“早买不了那麽久了,你家做买卖的,你是知道的,现在能去外边进货的谁还来这啊,我这里的生意虽说还没落魄到做不下去,但也只能早上那个点集中供应。整天宰的话,一是我也没那麽多猪,二是大家也没那麽大魄力一次拿那麽多,白日里再开一头我能宰到第二天去。”
“所以现在是只做早上生意?”
“没错,我认得你是南街饭馆的女儿,你们家一直从外边进货,不知道我这个猪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周传钰听到这里,说出了心中的疑惑,“那为什麽不办检疫证明呢?”
“姑娘啊,听你口音是从城里来的,你是不知道我们这些乡镇猪场的难处,”老板放下水管,撩起脖子上的白毛巾擦咯吱窝的汗,叹一口气,“我这儿宰的猪只有一半是自己养的,剩下全是河对岸村里散户自己养的。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这两年没这说法了,但还有好些人家留着着习惯,但也都不杀年猪了,只等养成了拉过了河,给我们这些宰猪场。”
“这麽多年过去,大家也都成了熟人,那边送来你硬是不收,这不是个说法;劝人农户下年不要养了吧,人少了一份收入不说,还会得罪卖猪崽的;可但凡收了一头,这检疫证明就办不下来,反正怎麽着都讨不到好。”
周传钰皱着眉点头,“这麽说是挺难的,我没想到这层。”
“哎,这也不是你们的问题,竈里多热只有烧火的人才晓得。”老板看向穆槐青,嘱咐道,“孩子,你姨我今天是和你们交心才这麽说的,你晓得吧……”
“清楚的,我们都清楚的,”她和老板相视一笑,摆摆手,“今天就是想来找点鲜猪肉,没买到就回去了。”
“好好好。”
老板出来送了一段路才返回去。
摩托停得有点远,两人沉默无言地走在河沙路上。
周传钰神色凝重地侧头看穆槐青,却恰好撞上她的眼神,只能开口道:“这麽看是能确定了,那个匡沛春私开货源,以次充好。”
不仅如此,甚至她戏还做了全套——用采购价从郭巧风那儿拿货,再低于市价卖给老街那个猪肉铺子,然後从北街肉铺买来到同样多肉,送去学校。
“这人真是哈……”周传钰都不知怎麽说她,哪里都有聪明但不用在正道上的人。
“她聪明就聪明在两头做账,反正数字是都对上了,就算是把账册子找了来,也看不清里头的弯弯绕绕。”
“对,”穆槐青表面不显,心里却一个头两个大,“即使我们想的一定对,也不好直接揪她的错,不然她到时候死不认账,还会反咬一口害了巧风姐。”
周传钰听了沉默下来,脑中捋着有没有破局之法。
思来想去,拿耗子还得先探探老鼠洞,“你在学校有熟人没有?”
“有倒是有,不过她不是管食堂的。”
“管不管食堂都得吃饭,可以问问她食材到底是个什麽情况。”穆槐青聚精会神等着下文,周传钰补充道,“最坏的情况也就是查不出淋巴肉来源,但大人说话比小孩有分量,如果学校里有人提了,怎麽说学校也会多注意一点。”
“也是个办法,这也是现在最近的突破口了,”两人坐上摩托,按照计划,往东边的老居民区去,路上穆槐青继续说,“那我找到空就去和那朋友琢磨琢磨,有进展了就和你说。”
“……也行。”老实讲,周传钰还是觉得这个人太过自来熟了,搞得像自己是她必不可少的探案搭档一样。
可实际上,她们认识才不到二十四小时。
一转眼周传钰就又在宾馆呆了两三天,出了这样的插曲,穆槐青得匀时间,暗暗查访,收拾房子的事自然就耽误了。
好容易收拾了出来,她便来宾馆接周传钰。
还带来个并不乐观的消息。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