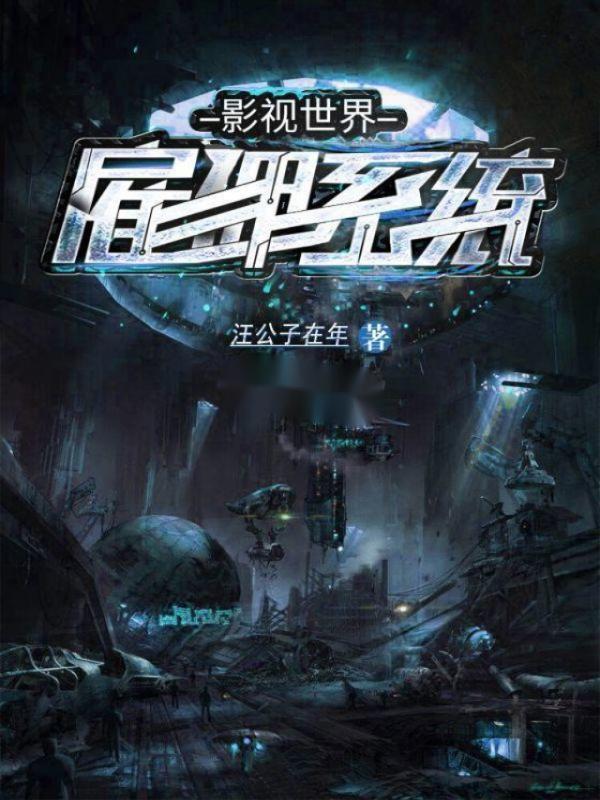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绘梦作品排行 > 原来是故友重逢(第2页)
原来是故友重逢(第2页)
“今日他说的那些梦境,场景多变,连无关紧要的吃食丶周遭环境都描述细致,我便判断,有几分假,如此看来,唯一真的,便是他母妃的死。”
唐砚知有些感慨,他弯下腰,用头蹭了蹭姜蕖头,道:“他定是没有忘记这个心结,七皇子除了地位威胁到他,还有七皇子母亲是怡妃的缘故。”
“皇上病中,意识有些混沌但时而十分清醒,今日我从混沌的阐述的梦境中看到了些东西。”姜蕖倾身去翻找,从衆多画卷中翻到了一张夜色浓重的画。
这幅画只有黑白色,屋内因窗外闪烁着闪电而映得亮堂,床榻上似有人颠鸾倒凤,仿佛这场暴雨是他们的狂欢,浑然不在意衣物撒了床前,突然间,还掉落了一件物什。
蜻蜓翡翠步摇。
那是皇上初遇宋菱时赠予她的,可此时送她这支步摇的人却站在床榻几米开外看着这一切。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皇帝从梦境醒来,惊出了一身汗。
“倒是曾听娘亲谈起,宫内外都曾传过菱妃与人私通,但并未有实质证据,加上皇上疑心重,後面她进冷宫病重,也并未派人医治。”唐砚知说。
“如此一来,成了梦魇。”姜蕖没想到能听到如此皇家秘闻,觉得颇为新鲜,不禁谈论起了这位天子,“久病之人总是被梦魇缠身,尤其是落下了心病的这种,我认为,你与翊王可朝这方面去查破,去年逆谋一事。”
唐砚知听她此言,笑叹她的聪慧,他屈膝蹲下来与她平视,“蕖儿怎知我要与翊王联手?”
“直觉。”姜蕖只说了两个字,但她心里都明白他是为了什麽,当初的江千衿是受他牵连而死,如今虽回来了,但他仍心有戚戚,若不将祸害连根拔起,他寝食难安。
双方彼此心知肚明,默契得没有提及,唐砚知只是深深地看着她,随即倾身吻了上去。
一吻结束,唐砚知将她拦腰抱起,送她回了卧房。他恪守礼节,并未上床,姜蕖擡眼看他,“你也该歇息了,都这麽晚了。”
唐砚知抚摸着她的脸,柔声说道:“你睡着了我便走。”
姜蕖本想嚷着不行,下一刻便被强制合上了眼,不过一会儿,竟睡着了。
看来是真的累了,唐砚知忍俊不禁,他起身又忍不住弯下腰亲了亲她,然後悄然离开。
过了几日,东宫传来噩耗,太子病重已是无力回天,仅过半月便薨世,举国哀思。
皇上得此消息更是差点随之而去,瑜王亲力亲为操劳着,连皇上身边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太子丧事料理结束,姜蕖发现唐砚知似乎更忙了,时常起来在府上都见不到他,在一次她应约前去给富家子弟绘梦时听闻,朝中似乎又要变天了。
果然,一个月之後,七皇子携数卷证据摊在了皇上龙塌之下丶也摊在了百官面前,彼时皇上还吊着一口气,似乎就在等着这一天。
瑜王被指控犯谋逆之罪丶陷害翊王丶害死太子等数罪,同时提及菱妃之事,他被当场压着做了滴血验亲,并非皇上之子!
于是瑜王败,翊王成为亶都太子。
事情似乎都尘埃落定,时间已然到了新春。
亶都的初春还是冷冽,山尖仍是积雪不化,但街道上已是淅淅沥沥。
姜蕖没出门,她躲在後院里得闲,听到身後渐近的脚步声也未回头,她知道是谁。
来人靠近了,她隐约间还闻到了梅花酥的清香味。
“新鲜热乎着,起来尝尝。”唐砚知蹲下来看她,见她休息的这段时间气色好了不少,顿觉心里开心。
“你忙完了?”
“抱歉,这段时日忙了些,没时间陪你。”
“无碍,我一个人待着也不无趣,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将亶都都转了个遍,哦除了皇宫。”姜蕖不喜那个地方,太压抑。
“蕖儿,跟我在一起,你开心吗?”自在吗?他没敢问出口,因为他知道,这偌大的亶都,实际是困住人的笼子,怕她觉得压抑,觉得没有在榛州自在。
“我开心呀!有你在,就开心。”
“那……如果与我成亲呢?”唐砚知试探着问。
“嗯?”这是唐砚知第一次提出这个,但其实他娘亲叶离提过许多次了,每次都被她打马虎过去,如今他提了,自己有理由拒绝吗?
想来是没有的,因为她也喜欢他。
“如果觉得太早……”
“好啊!”姜蕖笑着说。
唐砚知心中石头放下,一把将她入怀,激动得有些失态,“谢谢你千衿。”
突然被这麽一喊,姜蕖觉得有些不习惯了,“怎麽突然唤我这个名字?”
“那你喜欢我怎麽叫你?”
自从重生以来,她一直用的是姜蕖的身份,若突然叫江千衿反而引人怀疑。
“都可以,但明面上还是不变吧,免得多生是非。”
“好。”唐砚知雷厉风行,马上吩咐丁郝,“去告诉老夫人,找一个人算一下良辰吉日,安排我与蕖儿的婚事。”
丁郝顿时心花怒放,马不停蹄地下去禀告老夫人。
姜蕖擡眼望远山,蓦然想起来了在榛州的日子,“你说,婚期时,言靖和南烛会不会来?对了,还有晓念,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也没法向他们发请柬。”
“放心,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至于,会不会到此喝杯喜酒,那便不得而知了。”
翌日,亶都左迁御史大夫唐砚知府上发出告示,于五月初三定下良辰吉日,唐砚知与绘梦师姜蕖举行大婚,满城皆叹,热闹至极。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