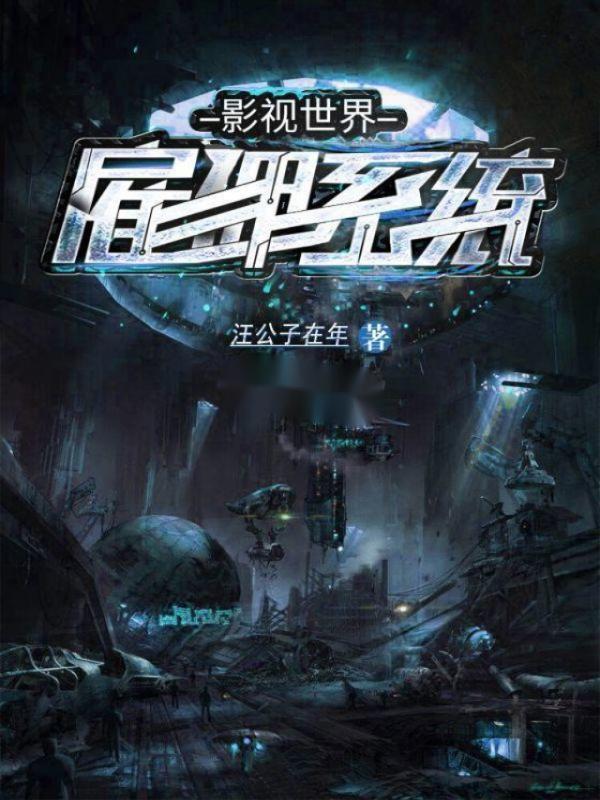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真少爷他求我复合重生 > 第62章(第2页)
第62章(第2页)
过了十分钟,手机猛然又振动两下,曾绍一口气差点没倒上来,只觉得天旋地转,堪比地震海啸来袭,他颤抖着抓起手机打开查看,谁成想那只是张霆发来的破行程表。
程之卓对自己,就连公事公办的态度都不肯维持。
长久的委屈在此刻爆发,化作莫名其妙的怒气,气得曾绍按语音键的指尖都在抖,“天要塌了还是屎盆子临头?什麽东西不能明早再发!”
对话框立刻显示正在输入中,但迟迟没有文字传来,这意思却明显,那就是勤勤恳恳的秘书张霆也在跳脚:大半夜的,您老发什麽神经?
但比起曾绍,至少张霆还没有失控,很快那一行提示消失,最後他发来一句:知道了!!!
黑暗中,粗喘声格外明显,曾绍看都不想看,脑袋直接撞进枕头里,差点抹掉後来那一声微弱的振动。曾绍把雪白的枕头搓揉来搓揉去,以为喋喋不休的又是张霆,又或者是哪个不识相的项目群马屁精,又又或者像刚才那样,不过是空白一片。
痴心妄想,痴心妄想!
可这麽翻来覆去好一会儿,曾绍心里还是不甘心,还是起来看了一眼,所幸多了这一眼,看得他蹭地弹起来坐直了,
程之卓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曾绍难掩兴奋地抓了抓头发,连发三次连删三次,看着对面发来的你好晕头转向。
最後曾绍指尖都冒出一颗颗细小的汗珠,却挑了最扫兴的一句发过去,“联姻只是为了维护集团,没有实际意义,早点休息。”
毕竟他俩之间,不是一句你好就能和好如初的,曾绍思来想去,还是想着先把误会解释清楚——即便在人家眼里,那或许根本算不上误会。发送键按下,曾绍忐忑不安地等了半个多小时,对面大发慈悲,终于发来一句知道了。
知道了,他知道了。
多麽美妙的三个字,能续曾绍足足三十年的命,他咧着嘴根本停不下来,闭上眼,梦里都是春天。
…
隔天何氏集团大办公室,工位上小刘接起电话,眼珠子一转,道:“我还要上班呢。”
说话间旁边的同事瞥了他一眼,然後照常继续工作。
那边小刘手指不停调节音量,接连嗯了几声,然後挂了电话和同事说:“我有事儿出去一趟,要是主管来了帮我打个掩护,拜托了。”
同事看他一脸急切,多问了一嘴,“要紧事儿?”
小刘怎麽可能愿意坦白,他只含混道:“女朋友闹脾气,非要我现在过去哄她,她就这臭脾气。”
“明白,那你可得快点儿回来啊。”
同事目送小刘出门,然後才往尤敬尧的办公室看了一眼。那头小刘毫不知情,一路小跑进了两条街外的咖啡馆,正对上坐在最里面角落的褚明伦。
小刘听褚明伦讲了大概的来龙去脉,抓住其中关键问:“死刑犯?”
“对,”褚明伦点头,“五年前协安医闹那家夥,没想到他身上背了不少外债。”
正因此小刘才十分不解,“那跟地下实验室有什麽关联?”
今早有关地下实验室的传闻忽然被辟谣,当时撰写文章的记者也已经注销社交账号,并被报社辞退。但褚明伦没和盘托出,那个死刑犯原先其实正是化工厂的员工,准确地说,正是那一批杀手之一。那年他提着斧头砍死俞主任,就是因为他的家人吃了俞主任开的药不治而亡,俞主任忌日都过了四五回,眼见死刑犯都要伏法,要是这时候顺着这个方向发酵下去,势必会引发公衆怀疑,整个药协是否都是一窝蛇鼠?所谓正义的药审程序背後究竟是否存在暗门?
“知道太多对你没有好处,”褚明伦言尽于此,反问道:“你要的理由我给你了,我要你做的事儿呢?”
小刘低头看了眼药剂,退避三舍,“可这是犯罪!”
“跟你之前做的相比,这能算什麽,”褚明伦冷笑道:“往好了说,这不过是助兴的玩意儿,只要你小心一点,谁能发现?”
“不行,真的不行!”
小刘不停摇头退缩,他原先想得天真,想着帮褚明伦做一回腌臜事就能得道高升,可现在看来,好像又不是那麽一回事。今天褚明伦说白了就是得寸进尺,就算下药不是犯罪,那明天呢?谁能保证一步一步走下去,前面不是万丈深渊?
“哦?”见状褚明伦靠上椅背,拿出一支笔,撂在桌上,那笔滚动两下,撞上小刘的咖啡碟,咔嗒一声停了下来。
“这,这是什麽?”
小刘不寒而栗,他这麽问,实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果真下一秒褚明伦点开录音笔,那天的对话铺天盖地灌进小刘耳朵,叫他想咬死不认都不行。
“你,你!”
“刘工,”褚明伦面对语无伦次的小刘,十分玩味地再次问道:
“想清楚了吗?”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