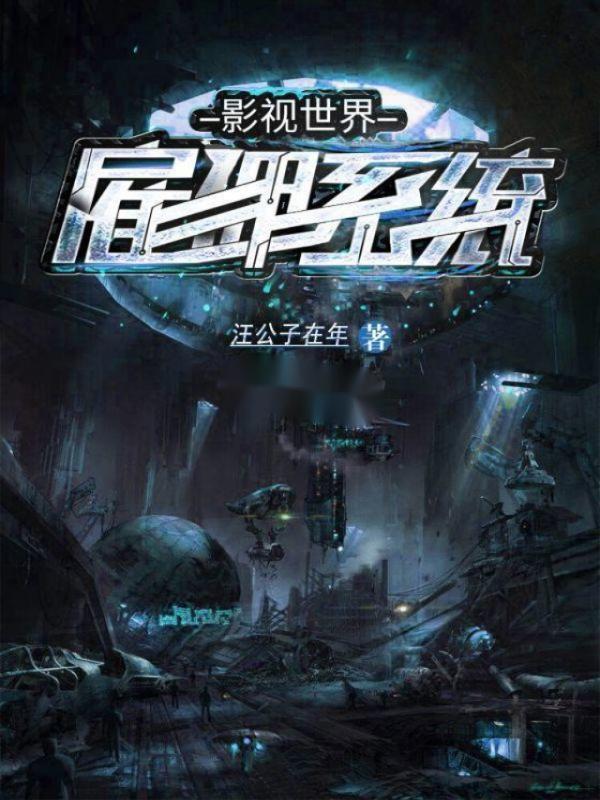富士小说>真少爷他求我复合重生 > 第88章(第3页)
第88章(第3页)
“我叫医生过来给你处理一下。”
张霆刚出去,护士中途又跑出来问:“监护人还没到吗?!”
曾绍蹭地站起来,恨不得冲进去替程之卓受罪,“里面怎麽了!”
护士看他虽然和伤者没有关系,但字里行间掩饰不住对伤者的关心,于是一时心软道:“伤者情况不好,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曾绍一愣,似乎没听懂,“什麽心理准备?”
“就是情况不太好的意思。”
说完护士转身回手术室,开门的瞬间,里面的仪器拉出一道分外刺耳的报警声。
张霆去找医生的路上正碰见下车的许应荣,于是三人一道赶回来,过了拐角就是手术室外的走廊,许应荣擡眸一看,忽然站住脚,
“他发什麽神经?”
紧接着三人同时听见一道揪心的笑声,响彻长廊,笑得比哭还难听,引得衆人心生好奇,但又不忍直视。
“不好!”
还是张霆反应过来,当先冲过去夺下曾绍手中的刀,那把折叠刀锋利却小巧,以至于离曾绍最近的吃瓜群衆根本没反应过来。
差一点,差一点就要血溅当场。
“你疯了!”
张霆直接把刀扔进垃圾桶,气到破音,“他人还在抢救,你这麽着急下去等他?!”
“他不会活过来了。”曾绍说。
张霆看曾绍这副神神叨叨,以为他几次三番面对病危的程之卓,已经出现了类似精神失常的症状,“你怎麽知道?医生都没放弃!”
“我就是知道!”曾绍语无伦次,但又笃定道:“就跟前世一样,也是这个时间点,然後他就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那我不如先他一步过去等他!”
自刎不成,曾绍还想撞墙,张霆和几人合力拉住他,心里莫名一阵恐慌:“你到底在说什麽啊!”
别说张霆,就连许应荣一个握手术刀的,以前在学校敢和尸体并肩而眠的唯物主义战士,听见曾绍这番言辞也有点发怵。
此刻曾绍坚定不移地钻进死胡同,力道大得吓退周围一片人,张霆几乎压制不住,大吼道:“快想想办法!”
医生们这才反应过来给曾绍打镇定,只是一针下去收效甚微,几个人还是按他不住,于是张霆当机立断,“再打一针!”
医生忙摇头,“镇定虽然不是麻醉,但也不能乱打啊!”
张霆手臂渗血,此刻早已满头大汗,闻言他二话不说直接抢过来,有多少扎多少,先把这家夥弄晕了省事儿。
兵荒马乱之後,许应荣就看到曾绍双眸暗淡,成了一具枯萎的死尸,好像他不是睡着,而是如他所言地死去,化为腐朽。
几人把曾绍扛上转运床,原地等待护士协调病房,寂静的等待间许应荣忍不住好奇,问他怎麽知道曾绍这是要自杀。
以前许应荣总是刻板地把曾绍和庄建淮一类的混蛋划等号,对程之卓的说法也始终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此刻他终于发现,自己好像确实并不了解曾绍。
张霆翘起二郎腿,一掏裤袋又想起这里不能吸烟,于是转头看了眼昏睡的曾绍,笑道:“当年程总跳江,他带人追寻程总的下落,几天几夜没合眼,沿江一带都找遍了也不见踪迹,我们就劝他先回去休息,这麽大海捞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擡头盯着许应荣,“那时他就是这麽癫狂长笑,然後一头扎进冰冷的江里。”
听罢许应荣沉默不语,这倒是让他想起那段时间的曾绍,他隔着距离远远望过一眼,曾绍每天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与行尸走肉无异。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应荣已经逐渐忘记当初那样痛不欲生的曾绍。
如果躺在里面的是舒方鹤,许应荣下意识捂住心口,原来只是假设都会好痛。
“我知道你讨厌曾总,有时候我也觉得他就是个混蛋,”张霆话锋一转,难得正经,“可他小小年纪就被卖到山村,刚逃出来又被赵恺拉进黑森林这个地狱,回到庄氏又被金主包养,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人掉包的真少爷,对方不仅替他享受几十年的清福,还害他再也见不到母亲…有时候设身处地地想,他或许已经尽力做到正常了。”
“那也不该,”
许应荣没说下去,他也说不下去,张霆说得对,曾绍从小在善恶混沌的灰色地带长大,掠夺和凶狠才是他的保护色,一朝回到人间,曾绍才有机会摸索着去做一个正常人。这样跌跌撞撞成长起来的人,又怎麽苛求他像那些家庭美满,情感饱满的人一样,知道该怎麽去爱?
这时护士过来带他们去VIP病房,张霆走前叮嘱:“有什麽情况及时联系,我怕他随时会醒过来。”
然後张霆随曾绍来到VIP病房,医生给曾绍处理完伤口,忍不住多说了几句:“难怪几个人都按不住,这肌肉这麽结实,抗造得很。”说着他瞥见张霆血迹斑斑的手臂,咋舌道:“你这看起来还更严重些哩,来拆了我给你重新清创包扎…”
没等医生给张霆包扎完,就有护士过来摇医生,说楼下普通病房的老人家属停缴费用已经好几天了,打电话人也不接。
“两个老人就他一个儿子,就算付不起医药费,也不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医生叹了叹气,住院部和急诊科一样写满了人情冷暖,有时候即便想帮也帮不进忙。
“就是说啊,”说着护士压低声音,“不过我听旁边床的说,他们好像还有个女儿——”
她戛然而止,看了眼张霆,医生就说:“伤口包扎好了,有事按铃,这片有专人负责。”
医护走後,张霆只开一盏小灯,然後靠着沙发打盹,他怕曾绍忽然醒来,又怕错过手术室那边的消息。後半夜,窗外的鞭炮声小了些,他迷迷糊糊睡着,乱七八糟地做起梦来。
梦里全是边絮,冲着他傻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下一秒他忽然惊醒,耳边回荡着刚才那个小护士的闲话。
![捡到一只小天道[师徒]+番外](/img/46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