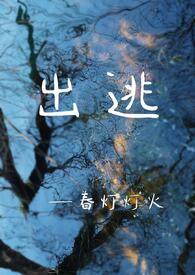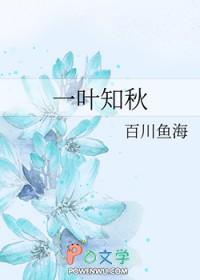富士小说>重生无限循环 > 3040(第15页)
3040(第15页)
公主会突然过来,当然不可能是她良心发现突然想起来还有个儿媳妇在这里,根源还是,沈寂要见她。
琴姑姑同公主交谈,这才惊觉,时间过的飞快,小殿下已过了会试,卷子已批了出来,殿下众望所归的中了一甲前十名。
周制,前十名将会殿试,由皇上亲自考核,裁定名次。
对谢家人来说,能进一甲足以证明嗣子的才学,个个面上有光,来道贺的人挤破门槛,名次未出,宴席已经不得不提前摆上了。似乎人人都认定,只要有资格入了殿试,那头名状元肯定是要落在谢无忌头上。毕竟那段过往,谁人皆知。高宗帝欠着谢家多年恩情,给个状元桂冠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人心里这么想着嘴上这般议论着,且谢孝儒已经听到风声了,还是从新进的贡生那里流传来的。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是姬后吗?这是要挑起谢家士族同寒门子弟的矛盾?
这么些年,姬后手中无兵无人,雍州士族集团紧密相连,她根本插不进去手,因此不得不拉拢一批被士族官员所排挤的庶族官员,利用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为自己巩固势力。而谢家自谢孝儒担任家主后,一直坚持家中子弟必须通过科举入仕,就是想缓和朝堂这种仇视敌对的情绪。毕竟世家大族若是想子弟为官,自有捷径可走。
捷径走多了,自然会招人恨。
谢孝儒为官这么多年,一直在官场上非常吃得开,受人尊敬,人人都肯听他三分劝,不仅因为他性格和善,公平公正,最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才实学,著书立说,利国利民。
他潜心教育儿子,只希望他也和自己一样,将全副心神用在朝政大事为国为民上,可沈寂刚得知自己中了一甲前十,作为父亲老怀安慰的同时问他想要什么奖赏,他开口第一句就是想见妻子一面。
谢孝儒一时倒忘了白驰已被送去雍州的事了,满口应下。等沈寂满心欢喜的去公主府,又被他母亲的人给拦住了。后来公主亲自过来跟他解释原委。
沈寂的反应没想象中的大,冷清清的,道了句,“果真如此。”
公主看他神色,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着急慌乱的解释、道歉。
就跟往常的很多次一样,由这件抱歉他的事总能延申到当初不得已将他抛下,亏欠了他很多很多,她想补偿他,尽她所能的补偿。殊不知,她每一次的道歉,都在一次次的提醒他,她是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孩子曾抛弃过他。
他永远都是不重要的一个,在需要做出选择时,只有他会被抛弃。这样的幽怨情绪无关大局,仅是他没有安全感的情绪发泄。
沈寂从写第二封信收到回礼就疑心了。他的小驰更多的时候只愿意当一个倾听者,她不是很温柔的人,不算细心体贴,可在她那里,他能感受到他这个人是独一份的特殊。如果有人要害他,她绝对第一个冲上前将他护在身后。
谢国公和公主不知道的是,从他发现他们联合起来骗他,他对他们的心门就死死焊上了。他将他们视作好师长好长辈去恭敬的对待、孝顺,可永远做不到当成亲生爹娘那样依恋亲近。
公主的道歉并不足以打动他,他心里很清楚,这样的上位者有很多种手段阳奉阴违。他们有太多门路和手段了,甚至会迷惑你,让你不辨真伪。他一直坚持写信,没有戳破,无非是想利用儿子的身份侧面敲打他们,他很在乎白驰,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她。
他不知道这样的敲打有没有效果。可笑,他现在竟然也有拿自己威胁别人的资格了?
他一直知道依赖别人的怜悯同情宠爱去获得某些东西是不长久的,因为依靠就意味着将主动权交到旁人手中。他若想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必须要自身强大起来。否则永远只能任人摆弄。
所以,他潜心刻苦,装作一切都不知道的样子,直到他考进了一甲前十。
他看着谢家长辈们欢欣快活的样子,他知道他有了谈判的资本。
公主告诉他,当初将白驰送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听说她在那边静心养胎住的很舒心,再加上月份越来越大,就没敢再折腾了。如果他的很想她,做娘的愿亲去一趟,将白驰给接回来。
沈寂当然不肯,他心里一直算着日子,白驰临盆在即,这样来回颠簸,还真是一点不顾及她的身子啊。
沈寂心中冷笑。
公主当然在乎,可是面对儿子的时候,她总是自私的先将儿子的需求放在第一。可怜她一腔老母亲的苦心。可悲的是,沈寂并不领情。
沈寂想去雍州,不用公主说什么,谢家长辈也是不允的。如今每日都有人上门道喜,还要设宴款待,他不在,像什么样子。说什么娘子怀身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大丈夫当以家国仕途为重,作为嗣子,谢门一族荣辱皆系己身,责任重大,切不可能犯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臭毛病。当年大禹治水,还三过家门而不入呢,他这算什么!
族中一位老太爷就说了,他爹就是太重夫妇之情了,差点叫嫡系一脉绝后。好在公主媳妇是个极好的,懂事孝顺识大局,处处为夫君着想,时时规劝,也为谢家牺牲了很多。他爹也争气,为了不叫公主受苛责,才一心仕途,强大自身。谢氏一门,虽有遗憾,也确真没人敢说什么了。要知道妻子的荣光可都是丈夫给的。
这时还有人击掌笑道:“等小金孙出世,无忌摘得状元郎,那才是双喜临门,要痛饮一番呢。”
因为还要准备殿试,当着文武大臣的面被考校学问,想着姬后必会刁难,朝中的庶族官员也都看着呢,他们必会倾全力出谋划策献计姬后。
虽然士族官员也会帮衬维护,可作为他谢孝儒的儿子,所有人嘴里没说,心里都在暗暗评估他能不能担得起下一代领头羊的责任,面子上都会维护他,可真正心里上的认可才最最重要。
这一场权力的斗争,老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才算是刚刚领进门而已,如果这一仗赢的漂亮,不仅能堵住寒门庶族的嘴,也能平息这一届考生的不满。有些暗潮涌动的流言自会不攻自破。
某些人不怕挑起矛盾,只怕在矛盾中不能获利。
谢孝儒叹气,他虽是士族集团中心,却深刻明白,平衡的重要性。尤其是朝政大权上,任何的一言堂,一家独大都不是好事。适当的争执,监督,不合,才能督促官员检省己身。人的贪欲是无穷的,而对手就是最好的治贪良药。
卫中丞曾嘲笑他人傻心软,明明可以一呼百应,有手段有能力,在姬后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将她一拳击垮。又在英王之乱后,趁着人才凋敝不大量安插自己人,非要进言陛下自下而上选拔贤才,开了庶族官员向上晋升的通道。这下好了,那群白眼狼是上来了,他们自怨自怜,抱团取暖,他们永不知足!他们攻击士族官员,他们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他们可曾感谢过你一句?
谢孝儒不被士族理解,亦不能被庶族接纳。他时常觉得自己游走在这二者之间,小心翼翼维护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他没有那通天的本事改变这一切,不能让人人都满意,他唯一所希望的不过是国运昌隆,百姓安居乐业。
姑且,这些都只能算作家事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内部纷争吧,他尚且还能游刃有余。
真正叫他忧心的则是,北边一直不太平。自前朝始,匈奴百余部落,逐水草而居,一直内斗不止,时有骚扰边境。当初李朝覆灭,除了末帝昏庸民不聊生之外,与匈奴大举进犯牵连兵力也有干系。后来李朝分崩离析,群雄逐鹿,高祖脱颖而出,建立大周。建国初期,也同匈奴结结实实打了几仗。高祖悍勇无双,自联盟大可汗被高祖亲手射杀后,匈奴退兵。自此后虽小战不断,却从无大战。
近十几年却听说匈奴也和部出了一位大枭雄,经过十几年的吞并,匈奴百部竟被吞并大半,此人自立为王,扬言要做草原唯一的王,自封“天可汗”。
谢孝儒早就注意到了,也曾提过先下手为强。匈奴不可统一,否则周国必危。然而英王之乱使大周国几代人的休养生息尽数折半,国库空虚。所有人都盼着太平,自上而下,无人愿战。
再加上英王是武将,反叛的时候,联合的也尽都是武将。事后被清算,不论是罪有应得的,还是无辜被牵连的,武将折了大半。就连名将吴近忧、蒙达也被牵连身死。有段时间,朝中简直跟中了邪一样,打击报复,互相诋毁,排除异己。
周朝元气大伤,经过这十几年重文轻武的发展。谢孝儒随手一划拨,心头比压了一座千斤鼎还沉重,朝中竟无良将可用。
而就在这时,天可汗竟手书一封国函给大周高宗皇帝,说要和大周商议北地十二州的归属问题。说从祖上开始,十二州就是他们的地盘,是被李朝夺了去,开垦耕地。如今他们要向开明的大周朝要回自己的土地。
这话简直是无稽之谈!
两国从年前就开始交涉,最终决定由也和部派使臣前来当面商议。如今使臣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谢孝儒暗自忧心,日夜苦思应对之策。
他满心的家国天下,又岂会在意家宅里的那点子小事。
而儿子考进了一甲前十,也算是对他近几个月来寝食难安的一些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