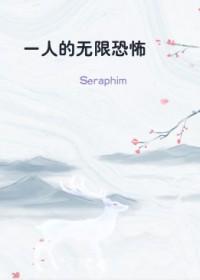富士小说>你眼中的星河 > 心要静(第1页)
心要静(第1页)
“心要静”
长信宫的晨光透过雕花棂窗,在宣纸上洒落细碎光斑。苏挽霓屏息凝神,望着皇後江疏影执笔,在她那幅墨兰图旁添绘一株并蒂兰。
笔尖游走,墨色淋漓。两人衣袖偶尔相触,苏挽霓的指尖微微发颤。
“心要静,”江疏影忽然开口,声线平稳无波,“手腕却需稳。”
“儿臣谨记母後教诲。”苏挽霓垂眸,目光却流连于皇後执笔的手——那双手骨节分明,早已看不出昔日挽弓射箭的痕迹。
珠帘外忽然传来通报:“太子殿下到——”
苏挽霓下意识後退半步,与皇後拉开距离。江疏影笔尖一顿,一滴墨落在宣纸上,缓缓晕开。
太子萧景煜笑着走进来:“儿臣来得不巧,打扰母後指点儿臣媳妇作画了。”他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流转,最後落在案上画作,“挽霓的画艺越发进益了,这墨兰颇有母後风骨。”
苏挽霓屈膝行礼,姿态恭顺:“殿下过誉了,是母後指点得好。”
江疏影淡淡一笑:“挽天资聪颖,一点就通。”她擡手示意太子坐下,“今日怎麽得空过来?”
萧景煜接过云釉奉上的茶,语气随意:“过几日春猎,儿臣来请母後一同前往。挽霓骑射出衆,正好可以陪母後解闷。”
苏挽霓猛地擡头,正对上江疏影的目光。两人心照不宣地想起那个秘密——苏挽霓苦练骑射,不过是为了复刻记忆中皇後纵马射箭的英姿。
春猎那日,苏挽霓着一身胭脂红骑装,发束金冠,竟与当年江疏影射落惊马时的装扮有七八分相似。
围场中,太子妃一骑当先,箭无虚发。萧景煜看得满眼赞赏,却不知看台上,皇後的指尖早已掐进掌心。
当苏挽霓策马归来,在马背上躬身向皇後献上猎得的白狐时,江疏影清楚地看见她眼底闪烁的光芒——那是在东宫从未有过的神采。
“儿臣谨以此狐,献与母後。”苏挽霓的声音清亮,带着几分压抑不住的雀跃。
江疏影接过白狐,指尖划过苏挽霓被弓弦磨红的手掌:“手怎麽了?”
“无碍的。”苏挽霓迅速收回手,耳尖却悄悄红了。
当晚营帐中,江疏影正欲歇息,帐外忽然传来轻叩。云釉掀帘一看,竟是苏挽霓捧着药膏站在那里。
“儿臣见母後今日似乎手腕不适,”她声音轻若蚊蚋,“特送来活血化瘀的膏药。。。”
江疏影看着她微红的眼眶,忽然明白她是找了个拙劣的借口。太子的营帐在另一头,她这般贸然前来,若是被人看见。。。
“进来吧。”皇後终是让开了身。
帐内烛火摇曳,苏挽霓跪在榻前,小心翼翼地为皇後揉按手腕。她的动作生涩却轻柔,呼吸微微发颤。
“母後可知,”她忽然低声开口,“儿臣第一次见您,不是在宫宴上。”
江疏影一怔。
“那年儿臣七岁,随母亲入宫赴宴,贪玩走丢了。”苏挽霓的声音如梦似幻,“在御花园的桃林里,看见您穿着一身绯色骑装,在练箭。那一箭射穿了三片飘落的桃花瓣。。。”
她的指尖轻轻拂过皇後手腕内侧一道旧疤:“您擦伤手腕时,用的也是这个味道的药膏。”
江疏影猛地抽回手。那道疤是多年前的事,连她自己都快忘记了。
“苏挽霓,”她第一次直呼其名,“你可知你在做什麽?”
太子妃擡起脸,眼中水光潋滟,却带着不容错辨的执着:“儿臣比任何人都清楚。”
帐外忽然传来太子的声音:“母後歇下了吗?儿臣得了些新鲜野味。。。”
烛火猛地一晃。苏挽霓迅速低头,掩饰眼中的慌乱。江疏影深吸一口气,声音恢复平静:“已经歇下了,明日再说吧。”
帐外脚步声渐远。苏挽霓擡眸,眼中满是惊惶与歉疚。江疏影却只是淡淡道:“回去吧,日後不必再做这种事。”
然而当苏挽霓躬身退出帐外时,江疏影却看见她遗落在地上的那盒药膏——盒底刻着一行小字:疏影横斜水清浅。
那是她年少时最爱的一句诗。
夜深了,江疏影摩挲着那行小字,忽然想起白日里苏挽霓策马归来时的模样。那身胭脂红骑装,确实像极了当年的自己。
只是那双眼睛,比当年的她多了几分不该有的情愫。
铜漏声滴答,仿佛在提醒着深宫中的界限。江疏影闭上眼,却挥不去那抹灼目的胭脂色。
太子萧景煜的脚步声渐远,最终消失在营地的嘈杂声中。帐内重归寂静,只馀烛火噼啪作响,映照着江疏影晦暗不明的面容。
她垂眸,指尖久久摩挲着那冰凉的药膏盒底,“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字样仿佛带着灼人的温度,烙进她的指腹,更烙进她沉寂多年的心湖。
那夜,皇後罕见地失了眠。帐外风声呜咽,却盖不住心底冰层碎裂的细微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