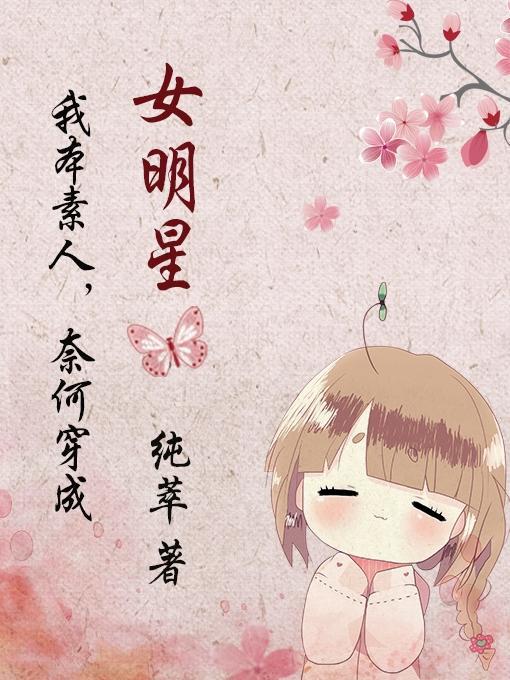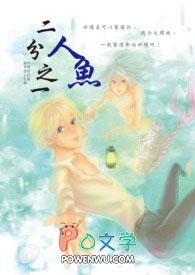富士小说>撂荒 > 新粮清点(第2页)
新粮清点(第2页)
最先动手的,是屋顶。
几场风雪之後,几间瓦屋虽然尚可遮风避雪,但林青禾清楚,极寒之下,一场狂风就能掀翻这类简屋。
她安排留守的青壮将院外搬回的木棍和石块压在屋脊与边沿,同时命几人剥下一些枯藤丶旧布,再糊上一层浆灰,将屋顶缝隙填实防风,必要处还加盖了油布。
王大爬上屋顶,一边笑一边拍打屋脊:“这回,就是野狼跳上来也刮不动了。”
二丶内墙糊灰泥
屋内也没闲着。
她让人拌上细土丶草灰与冷水,调成稠泥,一道道糊在屋墙与屋角,将缝隙堵死,尤其是靠风一侧,糊得更厚。
“这一层不光是隔风,也能防止热气散。”她一边用竹板抹墙,一边讲给正在干活的罗玥听。
罗玥眼睛亮亮地看着她:“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冷了?”
林青禾点头:“不会了。”
三丶加厚门窗封口
林青山带人砍来些粗树枝,加钉门板边角,又用废棉絮缠绕成条,堵住门缝和窗框缝隙。窗户四角都糊了灰泥,留了指甲宽缝透气,避免屋内炕热凝水。
林杏枝等人则将剩下的破旧衣物裁成门帘,挂于门後,再添一层挡风保温。
四丶炕道升级与烟道疏通
火炕既成,但还需细修。
林青禾检查每一间炕的烟道是否通畅,清除结霜,防止回烟;又用厚土加固炕沿,防止热量散失。
李漱兰又送来几张旧棉褥,衆人便裁成炕围,老人孩子坐上去便不想挪窝了。
五丶储水保温与应急准备
极寒天气出门取水不便,她让人提前装满缸罐,并将几口缸挪至屋内暖炕角落,以防结冰。
还让周晓萍和吴春花开始准备应急药草汤包,能驱寒通气,有备无患。
工程连着做了七八日,人人带着疲惫却也欢喜的神色。
“从没想过这屋子,能这麽牢实。”刘榆摸着墙角笑。
“那是林姑娘动的脑子。”孙冬生拍拍他头,语气里也带着几分骄傲。
*
雪未停,风未歇,城中却已悄然生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流。
五十来人的队伍分作数组,白日里各有分工:有人去城中为人做火炕,包吃包饭,晚上回院还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米粥;有人留守修屋整院丶劈柴打水,孩子们则一边帮忙,一边在雪地里追逐打闹,银铃般的笑声与咕咕炊烟交织,构成城西一角最温暖的光景。
吴春花一边搅着锅里浓稠的米粥,一边看着几个孩子围在竈台边等待,忍不住感慨一句:“这些日子,是这几年过得最舒坦的了。”
“正是呢。”有人笑,“咱们是托了林姑娘的福,这样的年景里还能有这般舒服的日子。”
衆人纷纷附和。
“她带我们过雪原丶熬风寒,还能教咱们做这火炕,换来吃食住屋,搁别人身上,咱们怕是连命都没了。”
“小石头前几天还哭闹得厉害,现在都胖了,晚上不盖被子都不冷!”
“我老娘也说,早不冷得喊骨头疼了,这火炕啊,真是神仙法子。”
有人说:“早些日子,我做梦都不敢想咱们能有今天。”
“是啊,那时候……路上人死一片,我想着,只要能活着到一个地方歇下就好了。没想到还能这样,一天三顿热饭,晚上躺炕上不冻脚。”
“要不是林姑娘,我们早没命了。”有人语气低哑,“她不带咱们,我们哪来的这顿热粥,哪来的屋子住?还敢想年後能在花溪城找个营生……”
“我打听了,春天一过,城里就要修驿道,还有码头,也缺人,咱们只要熬过这个冬天,就能留下来挣口吃的。”
“那到时候,就能自己买米买面,也不用靠别人施舍了。”
“咱们也不是只会伸手的人。”吴春花正回到屋子,“你们看看这些天,咱们换了多少粮,做了多少工,谁敢说咱们是白吃的?”
“对!”
衆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附和。
那一刻,林青禾望着眼前这一屋子的老老小小,忽觉这一路逃荒的疲惫仿佛都被炉火蒸发了一半。
她知道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真正艰难的冬月还在前头,花溪城未必能一直容得下他们,朝廷不定丶世道未稳……
但此刻,风雪之外丶屋檐之下,已经有了人间烟火丶有了希望的种子。
——她相信,只要人心不散丶脚不停下,他们就能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