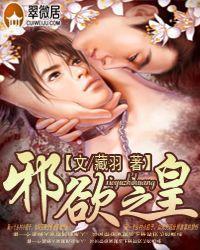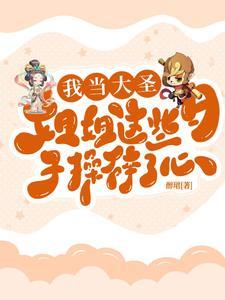富士小说>撂荒 > 秋收喜悦(第2页)
秋收喜悦(第2页)
这日,田里的青壮正埋头抢收秋粟,村中老人和孩子们则齐齐出动,专门去果园里采摘成熟的果子。
半大的孩子们个个跃跃欲试,争着爬上木梯,手里握着用竹竿削成的长杆。杆尖轻轻一挑,或是“笃笃”敲几下,枝桠便晃动起来,成熟的果子伴着细碎的叶子丶几根小枝条,“噗噗”地落下来。
树下早铺好了粗布,果子落下时被布面托住,不至于摔坏。
老人们守在布边,一边伸手去接,一边笑骂孩子们手脚太急——有的杆子还没伸稳,就使劲敲,结果果子没敲下来,自己先从梯子上滑下来,惹得满园的笑声。
布上的果子很快堆成小山,等一棵树摘完,几名力气大的便提着布的四角,把果子运到果园旁的小溪边清洗。
溪水冰凉清冽,冲刷过果皮时,那股酸香味更明显了。
挑拣的活最细致。
最好丶最饱满的一批野梨被分出来,直接切成片给大家尝鲜。梨肉水分足,咬下去先是一阵清凉,随後甜味在舌尖化开,带着一点点酸,十分解渴。
至于野枣……即便是最红的那一批,入口仍旧酸得牙根发麻,孩子们吃了纷纷吐舌头,嚷嚷“好酸”。
林青禾尝了一颗,笑着说:“这酸味,可正好拿来做蜜饯。”
刘大娘等几个年纪大的妇人当即点头,立刻着手处理剩下的野梨和绝大部分野枣。
做蜜饯的第一步,是切片。
野梨削去皮,去掉籽心,再切成均匀的薄片,整整齐齐摊在竹匾上;野枣则需先用竹签一颗颗扎几个小孔,好让糖水渗进去。
糖水的材料有两种——一是用与布依寨换来的蜂蜜,色泽金亮,香味浓郁;一是从镇上买回的蔗糖,虽然贵,却能做出口感不同的蜜饯。
蜂蜜版的蜜饯,需要将果子放进大陶罐中,一层果子一层蜜,密封好後放在阴凉处,让蜜慢慢浸透果肉;而蔗糖版的则要先熬糖水——锅里加水丶放糖,中火煮至糖溶化,再把果子倒进去,轻轻翻动,让每一片果子都裹上糖液,然後用小火慢慢收汁。
糖液渐渐变稠,果子也变得半透明,散发着甜香味。
晾晒是最後一步,也是最考验耐心的。
煮好的果脯得捞出来,铺在竹匾上,送到屋檐下或晒架上去晾。白日里晒太阳,夜里要收进屋,免得沾了露水坏掉。
为了防止苍蝇来叨扰,刘大娘和孟大娘特意用细纱做了几块罩子,轻轻覆在果脯上。
阳光下的果脯晶亮诱人,酸香与甜香交织,让人闻着就直咽口水。
做活的间隙,总有孩子在旁边徘徊。
刘大娘最会逗人,看见小青麦蹭过来,便笑着把手里的竹勺一收:“想吃啊?那可得先拿钱来买。”
小青麦歪着脑袋:“钱?”
“是啊,你要吃,就得先买。”
小青麦一听,立刻拉着在一旁发呆的小石头,神情郑重地说:“走,去找姐姐要钱!”
说完两个小人一溜烟跑了,留下一院子的人笑得直不起腰。
田间的林青禾正在割豆秆,见两个小家夥气喘吁吁地跑来,抹了把汗:“怎麽了?”
小青麦一本正经地说:“刘大娘说,蜜饯要用钱买,我们没钱。”
林青禾哭笑不得:“你们啊,糖都还没渗进去,就急着吃。”
小石头小声嘟囔:“可是,好香……”
田里的人一听,全都笑了起来,有人还喊:“青禾,给她们几文钱,让她们也当一回客人!”
林青禾便假模假样地从袖里掏出两枚铜钱,郑重交到小青麦手里:“拿去,买你们想吃的。”
两个孩子如获至宝,转身又跑回去了。
等果脯做好时,村里人人都尝过。
蜂蜜浸出的野梨片,酸甜温润,还带着淡淡的蜜香;蔗糖煮的野枣果脯,酸味已被甜味压下去,吃到嘴里有种黏软的回甘。
除了留给衆人解馋,林青禾还特意吩咐,从成山的蜜饯果脯里挑出一批色泽最亮丶形状最完整的,用竹匾仔细装好,准备在下个集日送去离人镇试卖。
这不仅是一份能带来银钱的副业,更是一场让所有人都能分到“秋收喜悦”的机会。
那些平日里因年老体衰丶或是抱着幼子不便下田的人,如今也能坐在院前,帮忙挑拣果子丶翻动果脯丶装篓封匾——手虽不沾泥土,却同样参与了村子的秋日丰收。
而村里的孩子们最喜欢这个活儿,不但能帮忙采摘丶切果丶晒干,还能顺便偷吃几颗——对他们来说,能在秋日的阳光下,一边干活一边吃甜的,这就是最好丶最幸福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