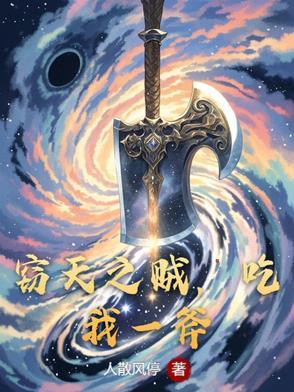富士小说>原来我就是陛下的白月光 > 第99章 凤仪初现慈宁宫(第1页)
第99章 凤仪初现慈宁宫(第1页)
沈清弦的身体在精心调养下,一日好过一日。谷底三日的磨难似乎并未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反而因祸得福,那双清澈的眼眸深处,更多了几分沉静与难以言喻的风韵,如同被山泉洗涤过的美玉,温润中透着内敛的光华。萧彻几乎将她捧在了手心,除了必要的政务,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主营帐陪着她,亲自过问她的饮食用药,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所有旁观者都清晰地认识到,这位贵妃娘娘在陛下心中的地位,已是无可撼动。
就在沈清弦基本康复,准备搬回自己营帐的前一日,一个意想不到的传召到了——太后娘娘请贵妃前往慈宁宫(围场行宫中的太后居所)一叙。
消息传来,锦书和添香顿时紧张起来。太后虽非陛下生母,但地位尊崇,且向来对后宫之事不甚热络,尤其之前因“妖妃”谣言和沈清弦种种“出格”行为,对这位贵妃印象并不算佳。此番突然召见,是福是祸?
沈清弦心中也有些打鼓。她对这个时代的“婆婆”天然带着几分敬畏。但避而不见是不可能的。她定了定神,吩咐锦书为她仔细梳妆,既要显得庄重得体,又不能过于张扬,失了病后的柔弱。
“娘娘,太后娘娘她……”锦书一边为她绾,一边忧心忡忡。
“无妨,”沈清弦对着铜镜,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陛下既在,太后总不会吃了本宫。”
话虽如此,当她踏入慈宁宫那间布置得古朴雅致、却处处透着威严的正殿时,手心还是微微沁出了薄汗。
太后端坐在上的紫檀木鸾凤椅上,身着绛紫色常服,头梳得一丝不苟,戴着简单的珠翠,面容保养得宜,看不出太多喜怒,唯有一双历经沧桑的眼睛,锐利而清明,此刻正落在沈清弦身上,带着审视与打量。
“臣妾参见太后娘娘,愿太后凤体安康。”沈清弦依足规矩,盈盈下拜,声音清越,姿态恭谨。
殿内一时寂静,只有檀香袅袅。太后并未立刻叫她起身,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足有十几息的时间,仿佛要将她里外看透。
沈清弦维持着行礼的姿势,脊背挺直,心中虽忐忑,却并未流露出慌乱。她知道,此刻任何一点失态,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终于,太后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听不出情绪:“起来吧,看座。”
“谢太后。”沈清弦暗暗松了口气,在宫人搬来的绣墩上侧身坐下,依旧垂眸敛目,姿态温顺。
“身子可大好了?”太后端起手边的茶盏,轻轻拨弄着浮沫,语气像是寻常的关切。
“劳太后挂心,已无大碍了。”沈清弦恭敬回答。
“嗯,”太后抿了口茶,放下茶盏,目光再次落在她脸上,这次少了几分审视,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复杂,“这次围场之事,委实凶险。皇帝……和你,都受苦了。”
沈清弦心中微动,太后这话,似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缓和?
“臣妾惶恐,未能护佑陛下周全,反累陛下涉险,是臣妾之过。”她连忙起身,又要请罪。
“罢了,”太后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事突然,非你之过。皇帝既然无恙,你也能平安归来,便是万幸。”
她顿了顿,话锋似乎随意地一转:“哀家听闻,那谷底三日,颇为艰难?”
来了!沈清弦心道,果然绕不开这个话题。她斟酌着词句,谨慎回道:“回太后,谷底确实……条件艰苦了些,幸得陛下庇护,方能化险为夷。”
她没有描述具体细节,更没有提及任何可能引遐想的内容,只将功劳归于萧彻。
太后看着她这副不居功、懂分寸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几不可察的满意。她活了大半辈子,在后宫见惯了形形色色的女子,眼前这个沈清弦,确实与旁人不同。有几分小聪明,懂得审时度势,关键时刻似乎也有些急智和韧性(能从谷底活着回来便是明证),最重要的是……皇帝对她,是动了真格的。
那山谷流言传得沸沸扬扬,皇帝非但不制止,反而隐隐有推波助澜之势,这其中的意味,太后岂能不懂?这是皇帝在用他的方式,为这个女人铺路,定名分!
既然皇帝心意已决,且这沈氏看起来也并非那等狐媚惑主、不堪扶持之辈,她这个做太后的,自然乐得顺水推舟。
“皇帝性子冷,自登基以来,哀家还从未见他对哪个妃嫔如此上心。”太后的语气愈缓和,甚至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感慨,“他肯这般待你,是你的福气,也是你的造化。”
沈清弦连忙低头:“是,陛下隆恩,臣妾感激不尽,定当尽心侍奉,不敢有负圣恩。”
“嗯,懂得感恩便好。”太后点了点头,目光在她依旧纤细的腰身上扫过,语气变得意味深长起来,“这后宫啊,说到底,子嗣才是根本。皇帝登基数年,膝下犹虚,不仅是哀家,前朝后宫,不知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沈清弦的心猛地一跳,脸颊不受控制地泛起红晕。太后这话……是在暗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