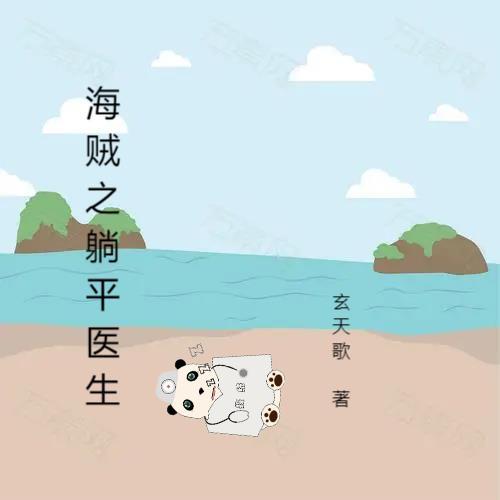富士小说>夺回家产资本家大小姐下乡边疆全文 > 第329章 送礼是门学问(第1页)
第329章 送礼是门学问(第1页)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后,屋内脚步声响起。
开门的正是王静娴,她穿着一件灰蓝色列宁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像章。
见门外站着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同志,她微微一怔:“同志,你找谁?”
顾清如笑道,“王同志您好,我是三营营部卫生员顾清如。”
王静娴眼神微微一动,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忽然笑了:“哦,是你啊,顾同志!前阵子兵团报纸上登过你的事迹,我看过那份报纸,这么一看果然是你。”
她说着侧身让开:“快请进,请坐。”
顾清如跟着王静娴走进家,竹篮放在脚边,规规矩矩坐在沙上。
她背脊挺直,双手放在膝上,不东张西望,也不伸手碰桌上的搪瓷缸、针线筐。
光是这份守规矩,就让王静娴心里点了头。
那些家属院里的老嫂子们,来了以后总是四处张望,
不是“这布哪买的”,就是伸手摸沙套厚不厚,更有甚者,翻起相册就问:“这是你家老江?”
还有的大嗓门,“哎呀,团长家收拾的就是不一样啊。”
“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布置的老好了。”
王静娴给她倒了杯热水递过去:“喝口暖暖。”
接着,她落座,笑盈盈的说,“顾同志,早就听说你了,这次农场防疫,又立了大功,小小年纪,真是不一般。”
顾清如接过茶缸,抿了一口热水,笑着说,“谢谢您,真是谬赞了。”
说着,她提起竹篮,轻轻放在矮桌上,解开毛巾一角,里面是一小袋晒的杏干盖在上面,像是随手带的零嘴。
“前阵子我弟弟上学的事,麻烦了王主任一家,还惹出一些风波。李嫂子说,这件事还让您费心出面调解,一直想当面道谢,又怕唐突。今天带了点家乡的小东西,不值什么钱,只是点儿心意,请您别嫌弃。”
王静娴看了一眼竹篮的杏干,没太在意。
刚来兵团随军时,这类“人情”她见得太多:鸡蛋、腌菜、鞋袜……大多是想求什么的前奏。
不过眼前这位不一样,顾清如刚在农场立了功,她不介意和这样有能力的年轻人多交好、走得近一点。
王静娴点点头:“你太客气了,刘玉香传瞎话的这种风气,在我们家属区就必须刹住。同志们在前线流汗出力,我们后方要是还搞这套传瞎话、拉关系的把戏,传出去像什么话?组织威信何在?”
“你今天来,这份心意我领了,以后经常来家里坐坐。”
见目的达到,顾清如也没多留,起身告辞,
“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改日再来拜访。”
王静娴意外之于客气挽留了几句。
人走后,王静娴收拾桌子,才把那篮子上盖着的蓝布掀开。
现那包杏干下面,还躺着一本书和一个小铁罐子。
拿起书来看看封皮,竟是一本鲁迅诗集。
这本书她也有,曾反复抄录其中诗句。可随军千里,行李受限,最终忍痛舍下许多书,这本便不在行囊中。没想到,竟有人同她一样爱读鲁迅。
她又拿起那一小铁罐茶叶,拧开盖子,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她只闻一下,便认出来了:这是明前龙井。
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雨前茶,也不是掺了茉莉花香的拼配茶,而是真正的头春嫩芽,色泽翠绿,形如雀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