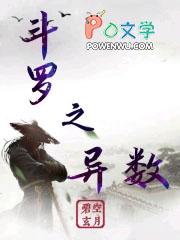富士小说>宫里接生婆叫什么 > 第239章 失传的回响(第2页)
第239章 失传的回响(第2页)
夜再度降临。
沈知微将《织声录》初本封入漆匣,正欲交付东厂快马传驿,忽闻外头传来轻叩。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小蝉站在门外,梢沾露,衣角泥泞,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她双手捧着一块粗布包裹的东西,递上前,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掌医大人……我去了一趟枫桥镇旧织坊。灶台塌了,我在下面……挖到了这个。”
沈知微接过,缓缓打开布包。
一块残陶片,边缘断裂,表面刻着半个“医”字,笔画古拙。
而在其下方,是一圈细密齿轮纹样,结构精密,竟与“天工引”图中的“节律环”如出一辙。
小蝉跪在门槛外,双手托着那块残陶片,指尖冻得青,声音颤抖如风中残烛:“掌医大人……我去了一趟枫桥镇旧织坊。灶台塌了,我在下面……挖到了这个。”
沈知微接过时,指尖触到泥土的寒湿与刻痕的锐利。
她低头凝视,呼吸一滞。
陶片边缘参差,像被烈火生生咬断。
半个“医”字横亘其上,笔锋苍劲,却带着女子特有的柔韧力道——是母亲的手迹!
她的心跳骤然失序。
而更令人震颤的是那圈齿轮纹样:精密、对称,每一齿距皆合黄金比例,其核心结构竟与“天工引”图纸中的“节律环”完全吻合,甚至……更早一步揭示了共振传导的力学原理。
她猛地翻开家传残卷,在最深处夹层抽出另一片焦黑布帛——那是母亲临终前藏入药囊的遗稿残页,仅存一行小字:“以声导气,以律通机,十二音振经络,百脉可复鸣。”
如今,两相印证,一切豁然贯通。
这不是巧合。
这是一条被活活斩断的血脉。
她的母亲不是疯妇,不是妄人,而是百年来第二位窥见“工医一体”天机的女人。
而当年那场所谓“暴病而亡”,恐怕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灭口!
沈知微站在灯下,指节死死扣住案角,指背暴起青筋。
她想起刑场第一刀剖开血肉时的滚烫,想起阿素第一次戴上“织脉带”时眼中重燃的光,想起赵嬷嬷说“她们的身子在喊疼”时枯槁的手掌——原来早在一百七十三年前,高祖姑母已听见;七十年前,母亲又接过了那一声呼救。
可她们都沉默了。
一个焚稿入山,一个葬身火海。
唯有她,站在这里,手握听诊器,身披掌医监紫绶,背后站着谢玄的东厂铁骑、三百织坊的劳作之声、万千即将苏醒的咽喉与手指。
她不能退。也不敢退。
三日后春分,日出东方。
京城西郊,“织医学堂”青瓦飞檐,匾额由皇帝亲题,却在晨光中被一抹更耀眼的光芒盖过——那是阳光穿过窗棂,落在沈知微胸前的听诊器上,血晶纤维泛出温润光泽,如同沉睡百年的血脉终于复苏。
她立于讲台,将改良版“织脉带”轻轻戴在阿素手腕。
阿素的手曾因长期操机而僵直变形,如今随着脉搏跳动,带中细丝微微震颤,传导至墙上的共鸣箱。
沈知微举起一枚铜梭,轻敲箱体——
“咚。”
一声清响,破空而出。
百里之外,三百织坊同时响起回应的节拍,整齐划一,如大地心跳,如万民同声。
城楼之上,谢玄负手而立,玄衣猎猎。
他手中攥着一封刚送来的密信:吴德全狱中翻供,供出先帝晚年曾秘密召见“沈氏女匠”,欲推行“工医一体制”,却遭太后联合礼部以“妇人干政、奇技乱纲”为由剿灭净尽。
他低声自语:“这一次,轮到我们掀桌子了。”
风起,纸页脱手,翻飞而去,掠过桑林深处,最终落在一座尚未命名的村口石碑上——泥胎未干,碑面空白,只有一行浅浅刻痕,似有人提前写下四个字的轮廓:
织声复兴。
夜渐深,学堂归寂。
沈知微独坐堂中,将小蝉带回的陶片与母亲残稿并列置于长案。
她取出阿素手绘的“天工引”机关图,铺展于壁板之上,目光久久停驻在共鸣箱与杠杆传感结构处。
烛火摇曳,映得她眸光如刃。
喜欢我,接生婆,掌中宫尺请大家收藏:dududu我,接生婆,掌中宫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