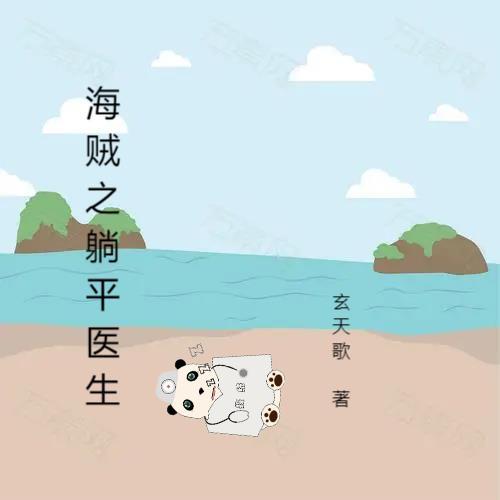富士小说>炮灰他只想求生免费阅读 > 伴读(第2页)
伴读(第2页)
于是,沈闻秋乖乖趴到凳子上,闭上眼准备迎接家法。
淮安侯见沈闻秋竟一句也不求饶,半点都没有对父亲的低眉顺眼,顿时更是火冒三丈,大喝一声:“打!”
秦姨娘见状,忙要扑上去,被早有准备的严青抓住,死死按在地上。
她无法,只能朝着沈闻秋的方向伸手,哭得身体一抽一抽的,嘴上喊着:“不要!不要打我儿子!侯爷!侯爷要打就打妾身吧,是妾身教子无方,都是妾身的错!别打妾身的儿子!”
瞧见秦姨娘的反应,淮安侯露出满意的表情,昂起头俯视着她和沈闻秋,道:“今日沈闻秋肯跪下来磕头道歉,好好行一行作为儿子的大礼!那我这个做父亲的,勉强可以原谅他。”
沈闻秋咬着下唇忍痛,没搭理姿态傲慢的淮安侯,他实在不是一个能忍痛的人。
但这会儿就是憋着一股气,他愣是给忍下来了,即便咬得嘴唇流血,留下深深的印子,双手握拳用力到极致。
忍得辛苦。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房门被推开,一名小厮冲进来,满面慌张。
“宫……宫里来圣旨了!”
淮安侯立刻站起来,满面惊慌。严姨娘则是一瞬闪过惊讶的神色,随机露出算计的表情。
至于秦姨娘,只一瞬间惊讶,便趁着严青震惊走神之际挣脱,朝沈闻秋扑了过去。
“闻秋,你怎麽样?快起来,别吓娘啊!”秦姨娘不敢触碰沈闻秋,生怕碰着什麽伤口。
沈闻秋说不出话,他这会儿疼得直哆嗦,却记得擡头朝秦姨娘摇摇头以表示他没事。
谁关心自己,谁又想要他死,他还是分得清楚的。
听说宫里来圣旨,淮安侯自是急着往外走。
可刚走了两步,他转身看向沈闻秋,皱了下眉,嫌弃地指了指屏风後,说:“快,把他弄进去,别冲撞了贵人!还有秦姨娘,也一并弄进去。”
小厮立刻点头应下,将趴在凳子上虚弱的沈闻秋架起来拖走。
担心沈闻秋的秦姨娘想上前,也被小厮按住,一并往屏风後拽去。
淮安侯赶到前厅,见宫中来的公公站在厅中,忙上前去,笑呵呵询问:“公公辛苦,犬子病了,方才去瞧他,竟耽误了招待公公,真是该死。”
公公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淮安侯,一眼便猜透淮安侯撒谎,笑着四处张望了一下,问:“贵府大公子在何处,这圣旨是给他的。”
淮安侯一惊,露出无措的神色,忙倾身靠近,压低声音追问:“不知公公可否告知一二,究竟是犬子做了何事惹怒贵人?”
公公皱眉,不满看了淮安侯一眼,道:“大胆!竟敢胡乱揣测天家!这是皇上恩准贵府大公子入宫陪九皇子读书!天大的恩赐!还不快快叫沈大公子出来谢恩!”
淮安侯哪里知道沈闻秋还能入宫伴读,只想起方才还将沈闻秋打个半死,顿时吓得直哆嗦,尴尬地扯了嘴角笑,解释道:“犬子……犬子病了,怕是……”
公公是宫中来的,什麽腌臜事没见过,瞧严姨娘和淮安侯那嘴脸,哪里还猜不到出了什麽事。只见他冷哼一声,道:“既是如此,那咱家自是要去瞧瞧病情如何,也好回宫向皇上禀报。”
淮安侯生怕叫公公瞧见沈闻秋的惨状,回宫说了什麽,忙给严青使眼色。
严青会意後连忙退下,跑到主院去,着急忙慌将沈闻秋送回到一处平日休息的院子去。
至于沈闻秋原先的住处,那实在不能见人。外边如何说淮安侯偏心不打紧,内里如何不能叫人真的瞧了去。
沈闻秋迷糊中只感觉到自己被人背起来,再睁眼只看见一名太监打扮的宫人站在床边,表情审视。
公公瞧了两眼,点头道:“确是病得严重,但宫中太傅开课在即,也不好拖久了。咱家回宫请示一番,若是皇上恩准,便请太医来瞧瞧,以免误了上学的日子。”
淮安侯本就没什麽出息,哪里敢惹皇上不快,当即答应着,“是,是,劳烦公公为犬子操劳了。这些日子府上也定当好好照看着,定不会误了上学的日子。”
公公满意地点头,说:“时辰不早了,咱家先回宫向皇上禀报。圣旨即是侯爷已作为父亲代为接下,那也不必折腾沈大公子,赶在上学之日前收拾妥当入宫便是。”
淮安侯连连应好,亲送了公公出府,才回到沈闻秋房中来。
他看着床上躺着的沈闻秋,盯着那张苍白的脸,心里头气不打一处来。
可他现在拿沈闻秋没办法,他没办法将沈闻秋送给瑞王,更没办法怎麽折腾沈闻秋。
方才再三保证,若到时候沈闻秋去不了,问罪的怕是他们全家。
淮安侯心里头不舒服,严姨娘更是气得咬牙。
凭什麽伴读这种好事轮不到她儿子,虽说九皇子失宠已久,但皇上都亲自挑了伴读,还郑重其事来瞧人了,定是上了心的,日後还不知如何呢。
一想到自家儿子的好机会叫沈闻秋抢走了,严姨娘心头便堵了一口气。偏偏圣旨已经下了,她也不好说什麽。
“父亲还是回去吧,儿子要休息了。”沈闻秋才懒得看淮安侯的脸色,他算是听明白了,他要入宫伴读,淮安侯暂时动不得他。
淮安侯听了,也不说什麽,冷哼一声,甩袖离开。
严姨娘也跟着离开,走时还瞪了秦姨娘一眼。
衆人走干净了,只留下一个秦姨娘,用帕子擦着沈闻秋的额头,露出担忧的笑容,含泪哽咽着说:“疼不疼?”
沈闻秋心头一动。
他险些忍不住眼泪,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当伴读这件事上边。
只有秦姨娘在乎他疼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