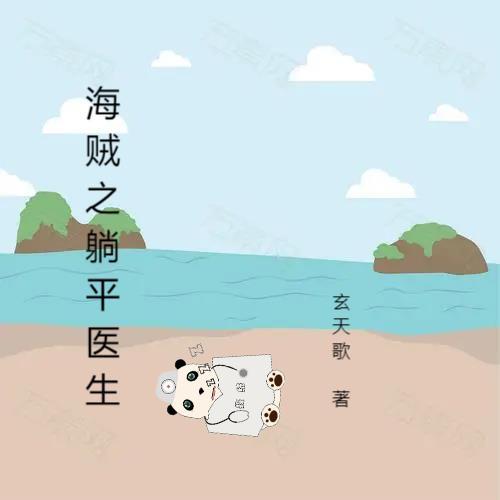富士小说>亡国后病美人成了新皇的笼中雀全文阅读 > 猫原来是自己在哭(第2页)
猫原来是自己在哭(第2页)
从前那些拿乔作娇的本事又有了是吧!
这段时间过得有些太平了,就得闹一闹是不是。
沈焕觉得一股邪火直往下冲,顿时转身上床,攥着袁茗的脚腕将人拉到身下。
“沈焕你干什麽!”
蜷在一侧的身体在沈焕手中轻易平展。
被男人眸中的野性刺痛一般,袁茗叫道:“不要!”
沈焕将他推搡的手腕压到头顶,居高临下道:“朕想做就做,什麽时候轮得到你说不了?”
他声音里沉着愤怒,将人占有。
袁茗刻意不配合他,沈焕用了力气惩罚,还是不得劲,心中越想越怒,火气从内烧到外。
沈焕终于耐心告罄,于是伸手拉开暗格,从中摸出东西,道:“想必是许久没用这些,你皮痒痒了是吧!”
他的声音仿佛从地狱传来。
袁茗像是听到了什麽可怕的耳语,更加用力地挣扎。
他知道,沈焕就是个恶魔。
这件事,他在去年今天就确定了。
为了让他屈服在身下,沈焕用尽了计策,软的硬的,或礼或兵,更不必说那些难以啓齿的下流手段,不知用了多少。
摧残他的身体,践踏他的尊严。
沈焕就像是一个胜券在握的猎人,冷漠地看着他在牢笼里冲撞得头破血流,最後怜悯地高高在上地,施舍般问他:“知错了吗,愿意了吗。”
他何错之有。
可是他只能向这无耻之徒跪地求饶,求一条生路。
“别这样,沈焕。”他惶恐得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沈焕无视他所有抗拒,对他的求饶充耳不闻。
他从金匮中拿出一个头戴红色珊瑚珠的长针,一寸寸扎进袁茗最脆弱的地方。
沈焕知道他最受不得的就是这个。
袁茗手脚被压制,急的哭出来,“你别……”
别作践我。
求你…
沈焕…
他没能将话说完。
银针贯穿灵窍的那一刻,袁茗觉得自己像是又回到那个噩梦里。
那些连绵秋雨,不见天光的日日夜夜。
他像引颈受戮的罪人,痛恨得泪流成河。
沈焕的影子在黑暗中被拉成可怖的形状。
他残存的意识被野兽吞噬……
半夜里,袁茗恍惚间好像听见猫叫。
一只小猫细细弱弱地叫了许久。
他後知後觉——
原来是自己在哭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