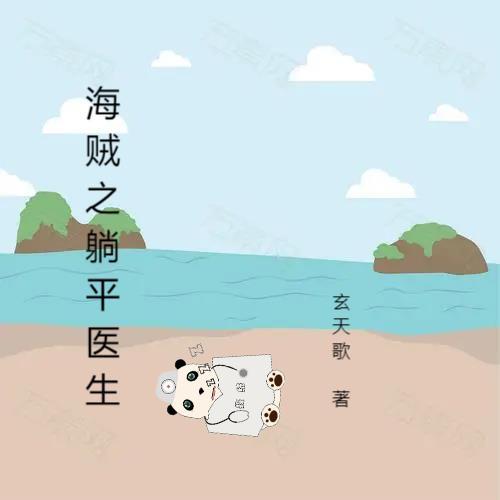富士小说>别当我傻子的经典语录 > 用尽伤人话(第2页)
用尽伤人话(第2页)
这句想脱口而出的话在喉间哽住。
阮误生否认了他的付出,拒收了他的礼物。
他把他彻底拒之门外。
于是他只能低下头,又一次说:“好吧。”
然後,像程序设定好的台词,他又一次说:“对不起。”
可为什麽要道歉呢?
为他的出现,为他带来的困扰,为他无力改变的现实,还是为他这份不被需要丶显得多馀的感情?
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
他只知道,除了道歉,他无话可说。
他总在爱里低头,卑微至极,又可笑至极。
阮误生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说“我们就断了吧”。
他没有原谅他,也没有丢弃他,他只是看着他,用那双被泪水洗刷得清亮的眸子深深地看着他,然後说:“再见。”
他给这段无疾而终的关系留下最後的体面。
可是真的还会再见吗?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後,或是人潮汹涌的街头,带着释然的笑,说一句“好久不见”?
连嘉逸看着眼前的少年,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忽然就笑了。
“不用再见了。”他说。
很多能给的东西我们此生早已给过彼此。
我的真心,你的眼泪,我的守护,你的傲气……所有炽热的丶痛苦的丶美好的丶挣扎的丶不堪的,我们都毫无保留地交付过了。
你最懂我的笨拙与任性,我也最懂你的无奈和骄傲。
既然相见只会互相折磨,既然靠近只会带来伤害。
既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是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那麽,
不用再见了,长辞永绝一定是我们最好的结果。
-
失魂落魄地走回家,连嘉逸没拿钥匙,他知道就算拿了也没什麽用,连谈不会让他进去的。
门外的锁已经撤去,他擡手敲门,过了好久连谈才出来,神情冷漠,“去见他了?”
连嘉逸嗤笑一声,连掩饰的力气都没有了:“明知故问。”
连谈点点头,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下一刻毫无预兆地擡脚踹向他。
他的动作让连嘉逸始料不及,伴随下一声闷响,双腿一软,膝盖重重摔在地上,痛得他下意识吸气。
“跪着吧。”连谈的声音从头顶传来,转身从屋里搬出一个椅子,放在连嘉逸面前,好整以暇地坐下,“惩罚。”
“还亲自看着我,时间真多。”连嘉逸忍着痛说。
“不看着你,等着你像以前那样对着监控挑衅我,然後偷跑去玩?”
“那最後不是绕着家里蛙跳一圈了麽。”
“闭嘴。”连谈不为所动,“跪你的。”
连嘉逸不再说话,他知道这惩罚肯定不止跪那麽简单,他的心底泛起一丝悲凉,连谈究竟是看到了什麽难以入目的东西,才会值得他这麽生气。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膝盖从剧痛变得麻木,再到酸胀疼痛,他不知道跪了多久,直到夕阳的馀晖将门口的地面染成橘红色,连谈才终于慢悠悠地站起身,拿起手机戳戳点点,似乎是在处理工作,又似乎是在确认时间。
“起来吧。”他命令道。
连嘉逸尝试移动,只是双腿却早已失去知觉,刚一用力,便是一阵酸软,差点再次栽倒在地,他勉强用手撑在地面,才稳住身形。
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最後一丝光线,家在此刻变成了刑场。
连谈近乎粗暴地抓住他的後衣领,那根他用来逃离的绳子,此刻被连谈握在手中,成了一条鞭子。
“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拳脚如同雨点般落下,夹杂着绳子的鞭打。
连嘉逸蜷缩起身体,试图缓解一下,但那疼痛无孔不入,从皮肤渗入肌肉,吞噬着骨骼。
他感觉自己的肋骨在哀嚎,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痛楚。
意识开始模糊,视线变得朦胧,在意识涣散的边缘,他听到自己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呢喃:“爸……我他妈……要死掉了……”
“死不了。”连谈适时收手,冷静道,“医生来了。”
再次恢复意识,是在医院消毒水气味弥漫的病房里。
病床上,他半阖着眼,朦胧间看见连谈进来,走到他床边,俯下身,靠近他的耳边:“下次再去找他,可不止一根肋骨那麽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