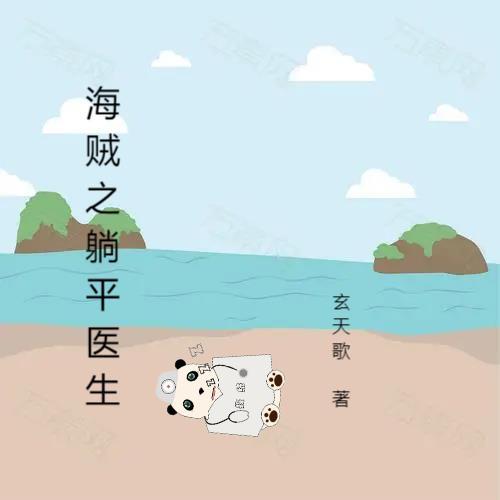富士小说>外卖偶救失忆富婆 > 第28章 通风管逃生(第1页)
第28章 通风管逃生(第1页)
第28章通风管逃生
老毒的嘲讽像淬了冰的锥子扎进两人心里,朱城康握着撬棍的手青筋暴起,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撬棍的金属柄被掌心冷汗浸得发滑。
他能清晰听见防毒面具滤毒罐的"咕噜"声越来越急促,罐身已经泛起淡淡的白雾——
毒气浓度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面具边缘甚至开始渗出细微的毒丝,再犹豫半分钟,肺部就要被神经毒剂侵蚀。
"不管通哪里,先出去再说!"
他咬牙将撬棍尖端嵌进锈迹斑斑的格栅缝隙,手腕发力时左臂伤口骤然抽痛,像有把钝刀在割肉,冷汗瞬间浸透贴身内衣,顺着脊背往下流。
金凌安见状立刻上前,左手扣住格栅边缘,右手搭在朱城康的撬棍上,两人同时发力,"哐当"一声将锈死的格栅撬飞,里面露出仅容一人佝偻爬行的管道,内壁糊着厚厚的黑褐色油污,黏腻得像未干的沥青,还挂着几缕沾灰的干枯蛛网,散发着霉变的铁锈味。
"我先探路,你跟在後面。"
金凌安弯腰钻进管道,膝盖刚碰到管壁就忍不住皱眉——
管道直径不足六十厘米,肩宽稍宽些都要蹭到两侧,必须弓着腰丶缩着肩膀爬行,胸口刚好贴在粗糙的铁皮上,冰冷的触感透过薄薄的作战服传来。
他咬着牙往前挪,手掌按在油污的管壁上,指尖能摸到凹凸不平的锈迹,爬过第一个九十度转弯时,後背的扭转动作狠狠牵扯到胸口旧伤,那是三年前西山火并时为护阿哲挨的枪伤,子弹擦着肺叶而过,虽已愈合,却在摩擦和牵扯时疼得钻心。
尖锐的痛感像无数根烧红的细针,狠狠扎进胸口的旧疤里,他闷哼一声,额头重重撞在管道壁上,扬起的灰尘簌簌落在防毒面具的镜片上,瞬间蒙了一层灰雾。
"怎麽了?卡住了?"
朱城康紧随其後钻进管道,膝盖不小心顶到金凌安的脚踝,才惊觉前面的人爬行速度骤然降了一半,几乎是在一寸寸挪动。
他伸手轻轻拍了拍金凌安的後背,指尖刚触到对方的肩膀,就摸到一片细微的颤抖,像寒风中的枯叶;透过面具内置的短距通讯器,能清晰听到金凌安急促的呼吸声,还夹杂着压抑的喘息。
"旧伤。。。。。。"
金凌安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音,刚说完就被又一阵剧痛逼得倒抽冷气,"胸口蹭到管壁了,疼得没法用力。"
朱城康心头一紧,立刻往前挪了半尺,让金凌安能稍微直起一点身子缓解疼痛,他自己则屈膝跪在管道里,後背尽量挺得平直,左臂因为不敢用力而微微悬空,掌心朝上托了托金凌安的大腿:"趴我背上,我驮你走,这样能少蹭到胸口。"
"不行!你胳膊还在流血!"
金凌安挣扎着想撑起身子拒绝,手腕却被朱城康攥得死死的,对方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带着不容置喙的决绝。
朱城康强硬地将他的身体扳过来,膝盖重重磕在管道壁上,发出"咚"的闷响,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尽量把後背挺得平直,像一张拉满的弓:"少废话!再耽误下去,咱们都得变成毒气罐里的标本!你胸口的伤再恶化,别说擡手的力气,连呼吸都会扯着疼!"
金凌安垂眼看向朱城康左臂的绝缘套,暗红的血渍已经晕开拳头大的一片,甚至顺着袖口往下滴,他终究咬了咬牙,小心翼翼地趴在朱城康背上,尽量把重量压在对方完好的右肩上,双手轻轻圈住朱城康的脖子。
朱城康闷哼一声,双手撑着管壁发力,指节抠进管壁的锈迹里,一步一步往前爬,每挪动一寸,左臂的伤口就被牵扯着疼一次,冷汗顺着下颌线往下滴,砸在管道壁的油污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很快又被後续的爬行动作蹭成模糊的印记。
管道内一片漆黑,只有两人粗重的呼吸声和身体摩擦管壁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像极了暗夜里的爬虫在蠕动。
金凌安趴在朱城康背上,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後背肌肉的每一次颤抖,还有左胳膊伤口渗血後,湿冷的布料黏在自己小腹上的触感——那是属于朱城康的血,温热又带着刺痛人心的重量。
他悄悄擡起手,轻轻按在朱城康的左肩,尽量分担自己的体重,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愧疚:"再坚持一下,林默说前面三百米处有个检修口,能暂时歇脚,我帮你看着方向。"
朱城康咬着牙没说话,只是加快了爬行速度,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贴在额头上,呼吸越来越沉重。
就在距离检修口还有两三米时,头顶的管道突然传来"咔嗒"一声脆响,像是生锈的金属支架不堪重负断裂的前兆,紧接着整个管道剧烈摇晃起来,管壁上的油污和灰尘大片大片往下掉。
"不好!管道锈蚀断了!"
朱城康反应极快,几乎在摇晃开始的瞬间就转身,用自己的後背和双臂死死环住金凌安,将他整个人护在怀里,後脑重重撞在管道壁上也浑然不觉。
下一秒,管道底部突然"轰隆"一声断裂,两人瞬间失重下坠,金凌安只觉得天旋地转,耳边全是呼啸的风声,还能听到朱城康在他耳边喊"抓紧我"。
下坠过程中,朱城康始终保持着护着他的姿势,後背先撞在一根悬空的金属管道上,发出"砰"的闷响,震得他喉头一甜,却依旧没松开手臂。
紧接着两人一起摔进一堆堆叠的木箱里,木箱被砸得四分五裂,里面的武器零件"叮叮当当"滚落一地,步枪的枪托撞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金凌安挣扎着从碎木片里爬起来,一把扯掉脸上的防毒面具,刺鼻的火药味和金属味立刻钻进鼻腔——他们摔进了一间武器储物室,四周堆着一人多高的墨绿色军用木箱,不少箱盖敞开着,里面的制式步枪丶军用匕首和手雷散落一地,金属零件滚落时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
他顾不上拍掉身上的木屑,连忙去扶压在碎木箱下的朱城康,却见对方脸色惨白得像纸,嘴唇抿成一条毫无血色的直线,左臂的黑色绝缘套已经被鲜血彻底浸透,暗红的血顺着指尖往下滴,砸在武器箱的木板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连右肩也因为刚才的撞击而红得发亮,轻轻一动就疼得他倒抽冷气。
"你怎麽样?是不是伤到内脏了?"
金凌安伸手想碰他的左肩,却被朱城康突然攥住手腕,对方的力道很大,指节泛白,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到鼻尖几乎相触,彼此的呼吸都喷在对方脸上,带着汗水和淡淡的血腥味。
就在这时,储物室的铁门突然被"哐当"一声推开,刺眼的白炽灯光从门外射进来,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伴随着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凌安?真的是你!"
金凌安猛地擡头,只见门口站着个穿黑色作战服的男人,作战服左臂绣着"寒刃"的银色刀刃标识,领口还别着当年队里的专属徽章,手里举着一把USP手枪,枪口却微微下垂,离扳机还有半寸距离,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挣扎——
那是李响,他当年在"寒刃"最要好的队友,两人曾在漠北的雪地里互相抱着取暖,也曾在执行任务时为对方挡过子弹,李响的妹妹出嫁时,他还偷偷去当过伴郎。
李响的手指死死扣在扳机上,指节泛白,却迟迟没有发力,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音,目光在金凌安和他身边的朱城康之间来回扫视,最後又落回金凌安脸上,眼底翻涌着失望和不甘:
"他们说你背叛组织,勾结'烈焰'的叛徒朱城康,害死了队里三个兄弟,还泄露了西山地库的布防图,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