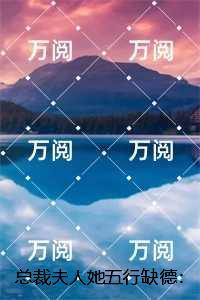富士小说>人潮人海中是什么歌曲的歌词 > 第209章 第二百零八章 这哪里只是多读了几本书(第2页)
第209章 第二百零八章 这哪里只是多读了几本书(第2页)
毒贩还注意到,“先生”对他总是更温和些,就越发认定“先生”在生活里的身份不一般。
他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总想着以後洗白上岸了,能通过“先生”这条线换一个清白点的生活。
而这样的想法还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老大喝多了说漏嘴,说“先生”一直都在岸上,随时都能洗白,就看他愿不愿意。
他当时就问,是不是他们以後也能跟着“先生”上岸?
老大却笑着反问:“他什麽脑子你什麽脑子?上岸了你喝西北风去啊?除了这个你还会什麽?”
老大的意思是,只要不得罪“先生”,好好供着,再熬个五年,攒够钱大家就收手。
毒贩听了,心里却另有想法,有一次抓住机会多和“先生”哭穷了几句,说是家里孩子等吃饭,婆娘抱怨说钱不够花。而要将这些货散出去,再等资金回来,还要一轮轮洗白,那都是几个月以後的事儿了。
当时大家都戴着防护面具,看不清“先生”的表情,“先生”听了只说了一句,叫他婆娘找个信得过的亲戚开个户,去买一只股票。但最多只能在手里攥十天,十天後赶紧抛出去,赚到的钱虽然不多,应急足够了。
这事儿毒贩印象非常深,说起来还有些後悔,就是因为家里的婆娘半信半疑,又舍不得钱,怕扔出去回不来,当时投入的不多。
没想到十天後净赚了八千多块。
当然,这八千多块不算多,可对他们来说,这事儿不仅合法,钱还是干干净净的,不需要付出半点劳动,更不必承担风险,纯属“白拿”。
而这八千块都只是因为对方的“一句话”,那要是多投一些,八万块不也能赚到吗?
那之後,毒贩就越发谦逊,还买了本书跟着学说话的艺术。
他偶尔也会从“先生”口中听到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学术名词,记住几个,私底下上网一查,都是些经济学术语。
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一听就觉得不明觉厉,然而在“先生”看来,都是日常的常用语,有时候说话会不由自主地带出来。
不过直到这一步,仅凭这毒贩的脑子,依然猜不出来“先生”的身份,还以为是“先生”多读了几年书才懂这麽多。
但这番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到了警察那里,很快就得出几种可能性。
这哪里只是多读了几本书?
大多数学生读十几年的书,出了社会到“先生”这个年纪还能记住几个学术名词?还能张嘴就精准道出必挣钱的投资方向?
而从犯罪心理上分析,这个“先生”也是颇有城府。
他提供的那只股票是只小股票,当时涨幅有限,再加上购买上限规则,即便毒贩砸锅卖铁全家投入,也不会一夜暴富,最多挣个“应急钱”。
那麽这笔“应急钱”就只能算是小恩小惠。
真要是给了大恩,下一次就该挟恩要挟了。
再说这毒贩,後来逃到外省被抓捕,将这件事说了出来,希望能算一次立功。
可是像是这样无名无姓,只有一个故事的供述,连“功”的边儿都沾不上,最後判的依然是死刑。
这个故事传回春城市局时,周岩警官在世时追查的制毒丶贩毒案已经算是告一段落,可以画上句号,唯有这段笔录留了一个鈎子。
再提起这茬儿,还是从江进开始不着调,多次违法纪律开始。
王队知道想保他,就得从根儿上处理,这才有了给戚沨的几份档案。
戚沨说:“那几份档案我研究了一段时间。说实话,仅从犯罪过程来解读,根本无法肯定徐奕儒就是‘先生’。直到李成辛提到这个名字。我想,一个在监狱内表现良好,不仅因为专利减刑,还帮助其他囚犯的模范犯人,为什麽会被李成辛的特别关注呢?也许是他某个时候的某个行为露出了端倪。那之後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李成辛请喜酒当天,我听一个从外省赶来的老同学说了个案子。那个嫌疑人来自单亲家庭,父亲常年酗酒丶赌博,家里一直欠着债。他能把大学念下来,完全是因为一位老师的常年资助。後来他当上财务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假账挪用公款。但那些钱他也是不用来给家里还债,他父亲早就因为酗酒死了。他说自己就是想要钱,源源不断的钱,看着那些数字存在自己的卡里才有安全感。之所以当时聊起这件事,就是因为说起这个嫌疑人的老师,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入的狱。”
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三个人和戚沨提到同一个名字,而且还涉及到犯罪,真是很难不留心。
“那宋昕……”夏正再一次开口。
戚沨说:“他一直隐藏得很好,也是徐奕儒所有学生里最得真传的一个。但真的查到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张魏的教唆案。不,那次只是一个开始。事实上即便是当时已经有了关注,我依然没有将他和徐奕儒联系到一起。”
许久不说话的江进这时开口:“宋昕提供的张魏心理咨询的内容,我也看了。但我没有发现。”
“就是徐奕儒?”
“是。”
作者有话说:红包继续

![(HP同人)[HP]命运·千年篇+番外](/img/157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