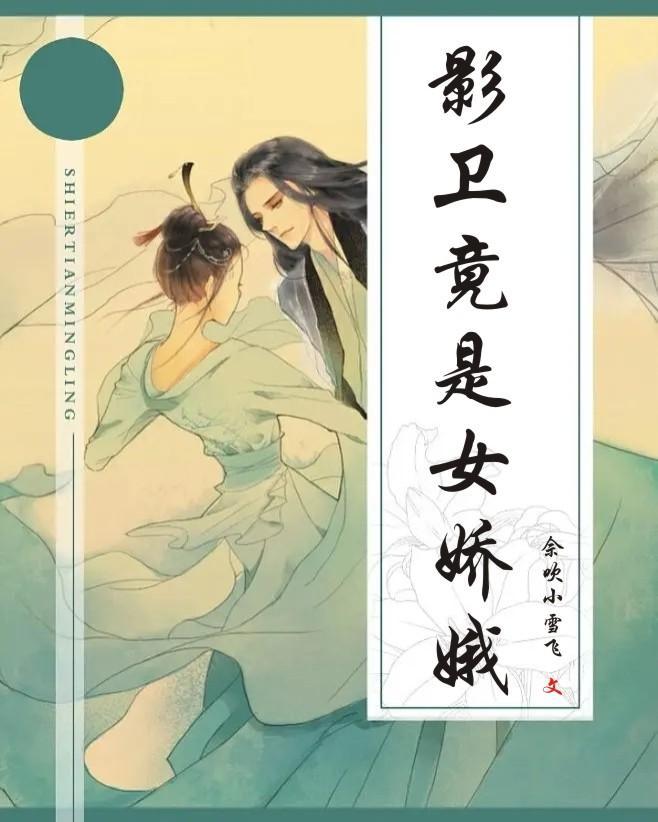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催眠我的家人0.7 > 第5章 完(第11页)
第5章 完(第11页)
在用这个姿势,将她再次操干到浑身抽搐、淫水横流之后,我将她从床上翻了一个身,让她像一只最温顺的母狗般跪趴在床上,将她那两瓣丰满挺翘的屁股高高地撅起。
我从她的身后,扶着我那根早已被她的淫水润滑得闪闪亮的巨大肉棒,再次对准了那个还在微微收缩的骚穴,狠狠地捅了进去!
“噗嗤!”
“呜……”
从后面进入的姿势,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我那根巨大的肉棒,是如何一点点地被她那紧致的骚穴吞没。
也让我能够更加方便地伸出手,去玩弄她面前那对随着我的撞击而不断晃动的巨大奶子。
我抓着她的腰,将她死死地按在床上,然后开始了新一轮更加狂野、更加原始的冲撞。
我将她当成了一个只属于我的可以任我泄所有欲望的性爱玩偶。
我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甘、所有的占有欲,都凝聚在我胯下的这根肉棒之上,然后一次又一次狠狠地全部泄在了这具属于我母亲的完美身体之中。
……
我的鸡巴在她那被“海王星II型”g点潮吹增幅器和无数螺旋形肉褶彻底榨干之前,终于抵达了爆的临界点。
那股汹涌的欲望,混合着对那个肮脏王子的无尽憎恨,以及对眼前这具成熟胴体最原始的占有欲,终于凝聚成了一股即将喷薄而出的滚烫洪流。
我死死地掐着她的腰,将她的身体更深地按向我,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她骚穴深处那个还在不断引她潮吹的g点,进行了最后几十下狂风暴雨般的猛烈冲撞。
“啊……啊……主人……要……要被主人的大鸡巴……操死了……婉儿……婉儿的骚穴……要被主人的精液……给灌满了……”
在我最后的疯狂冲刺中,她那被程序控制的身体,仿佛也预感到了我的即将到来。
她喉咙里出的呻吟,不再是之前那种纯粹为了取悦而出的淫荡叫声,而是带上了一丝……一丝只有在真正承载了生命的欢愉中才会出现的充满了渴求与迎接意味的奇妙颤音。
婉儿……
这是我第一次,从她的口中听到她在这个人格下的自称。
这个现,像一根最细微的毒针瞬间刺入了我那早已被欲望和愤怒填满的心脏。
它没有带来疼痛,反而激出了一种更加病态、更加扭曲的兴奋。
“婉儿……”我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嘶哑声音,在她的耳边重复着这个名字,“我的好婉儿……张开你的骚穴,把儿子的大鸡巴……把主人的精液……全都给吃下去!”
“是……主人……婉儿……婉儿要把主人的精液……一滴不剩地……全都吃到……子宫里……啊——!”
伴随着她最后那声响彻云霄的尖叫,我的身体猛地一弓,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更加滚烫浓稠的精液,如同积蓄了三年的火山,终于在我最原始的嘶吼中轰然爆!
我将那充满了我占有欲的滚烫精液,一波接着一波毫无保留地悉数灌进了她那具属于我母亲的身体最深处。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的精液正冲击着她那紧闭的子宫口,仿佛要将我的印记永远地烙印在她血脉的源头。
射精的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当最后一滴精液也流尽时,我浑身脱力地趴在了她的身上。
我的肉棒依旧深深地埋在她的身体里,感受着她那湿热的骚穴,因为我精液的灌入而在一阵阵满足地痉挛、收缩。
我没有立刻拔出来。
我享受着这种将她彻底填满的极致占有感。我将脸埋在她那充满了汗水和成熟女性体香的颈窝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婉儿……”许久之后,我才缓缓地抬起头,用一种充满了情欲和探究意味的眼神,看着身下这个被我操干得面色潮红、眼神迷离的女人,“告诉主人……跟那个肮脏的王子比起来……是他的鸡巴大,还是主人的鸡巴大?”
听到我的问题,她那双因为情欲而变得水汪汪的温柔眼睛里,闪过一丝程序化的光芒。
然后,她用一种充满了崇拜与谄媚的语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当然是主人的……主人的大鸡巴,是婉儿……是婉儿这辈子吃过的……最大、最硬、也最舒服的鸡巴了……”她的声音因为刚刚经历过激烈的情事而显得有些沙哑,但那份属于“温柔人妻”的谄媚与顺从却丝毫未减,“那个王子……他的鸡巴又小又软,跟主人比起来……简直就像一根没长大的小牙签……根本……根本满足不了婉儿……”
我知道这些话都是被设定好的程序,是“服务型人偶”为了取悦新主人而自动生成的标准答案。
但这一刻,我宁愿相信这些话都是真的。
“是吗?”我满意地轻笑一声,然后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她那被我操干得一片狼藉、此刻正不断向外流淌着我精液的骚穴,用一种充满了占有意味的语气说道,“那以后,你这具身体,你这个骚穴,就只准吃主人的大鸡巴,听到了吗?”
“是,主人。”她用一种近乎虔诚的语气回应道,“婉儿的身体……婉儿的骚穴……婉儿的一切……都只属于主人一个人……”
“很好。”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我缓缓地将我那根已经开始有些疲软的肉棒,从她那泥泞不堪的骚穴里抽了出来。
“噗嗤……”
伴随着一声淫靡的水声,一股混合了我的精液和她的爱液的白色粘稠液体,顺着我的肉棒从她的穴口汹涌而出,将我们身下那片洁白的床单,染上了一大片暧昧而又淫荡的痕迹。
但是,我并没有就此满足。
对于这具被那个肮脏王子玷污了三年的身体,一次骚穴的内射还远远不足以将他留下的痕迹彻底覆盖。
我的目光,缓缓地移动到了她那因为跪趴的姿势而显得愈挺翘丰满的屁股上。
在那两瓣浑圆的臀肉之间,一个因为细胞修复液的滋养而恢复得如同处女般紧致粉嫩的菊花,正静静地闭合着,仿佛在等待着我的临幸。
“转过去。”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说道,“把你的屁股撅到最高。”
“是,主人。”
她再次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我的命令。
她将自己的身体,调整成了一个最标准、也最方便被从后面侵犯的母狗跪趴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