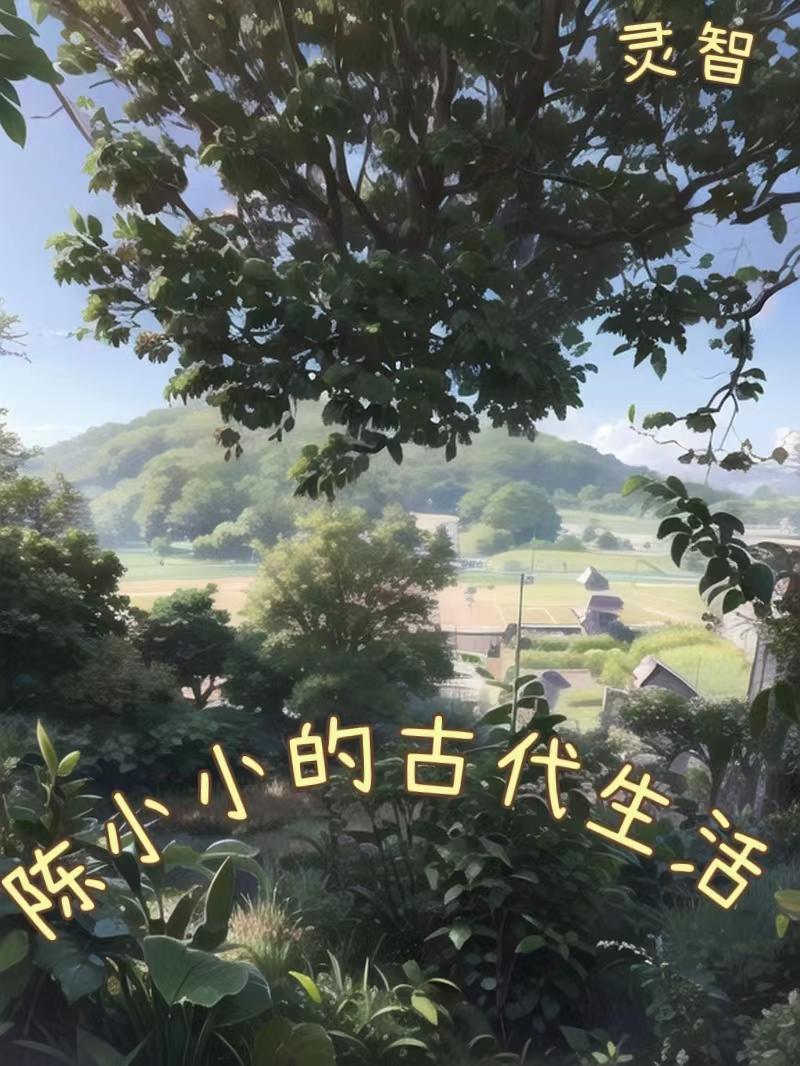富士小说>枯桐叶落枝梢折 > 第六十五章(第2页)
第六十五章(第2页)
花浔芊把报纸给她,师承志啧啧称叹,席间衆人也说想看,报纸传过来,孟怜笙接过一看,上面写了一篇写她那出《游龙戏凤》的戏评,辞藻考究通篇夸赞。
转眼间其他戏子也收到了写自己戏评的报纸,北方几位有名有姓的大角儿都有了,独孟怜笙两手空空。
这时衆人目光不免时不时落在孟怜笙身上,孟怜笙若无其事的吃了口果盘里的水果罐头,并未对这些目光有任何不适。
他忽然想起薛良所说那位包厢里的“狐朋狗友”,为表薛良的重视还是该问候一下,他简明扼要地说了一句,就出了宴客厅。
他敲了敲门,见到包厢里雌雄莫辨的孔令希愣了一下,心想薛良的朋友还真是千奇百怪,他将果盘放下,随即微笑道:“这位贵人,我们招待不周,您多担待。”
孔令希正玩弄西装袖扣,闻言一脸不耐烦地擡起头,见到孟怜笙这张脸时眉宇间的嗔锐气消失地无影无踪。
“你是孟…怜笙?”
孔令希声音脆朗,不过孟怜笙还是能听出这是个女性。
“嗯,是我。”
……
孟怜笙本想客套两句,谁知这孔二小姐十分健谈,拉着他闲聊了十分钟才算完。
孟怜笙回到宴客厅时他们仍在讨论报纸,刚落座姚苑芳突然碰了碰他:“孟老板,这写的是你啊。”
孟怜笙顺着姚苑芳的手指看,见黑白报纸上标题赫然几个大字:评孟郎之戏剧。
另外几人翻报页的手都依次顿住,随後齐齐擡眼看向孟怜笙。显然他们的报纸上跟姚苑芳的印着同样的内容。
孟怜笙接过报纸细细看来,这篇戏评写了老长,可却不像是个懂戏的人所写,非是讲戏,而是讲他。
收到报纸的几人将报纸翻看得刷刷啦啦,梅竹修不耐道:“这是写了多少啊,怎麽还没完。”
孟怜笙逐字逐句的看了两段,越看脸上越烧得慌,迟遥风凑到他旁边看,孟怜笙刚要把报纸遮住,无奈还是被迟遥风看见了。
迟遥风瞪大眼睛指着报纸:“我去,谁戏评写成这样,这是情书吧!”
衆人本没细看,听了这话又纷纷默读,花浔芊笑地耐人寻味,她拍了拍孟怜笙的肩,打趣道:“孟老板,这是哪位被你迷了心的戏迷啊。”
孟怜笙不答,他也想不出来。
“呦,这还提梅老板啊?”
听徐小奎这麽一提,衆人目光都落到这句上:“古之宋玉,今之梅旦,比之孟郎,差甚远矣。”
孟怜笙看到这皱了皱眉,怎麽能拿梅竹修和他做比较?梅竹修生得多好看啊。
又是几页旖旎缱绻的句子,中间穿插放了孟怜笙几场戏的剧照,这些久经风月场的戏子忍着肉麻终于看完了。
这篇戏评本就够使人观之色变了,看到结尾落款时在场的男男女女都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孟怜笙因为是这篇戏评的主角看得慢了些,他才翻到最後,只见落款立着俩他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大字:薛良。
孟怜笙脸色总算好看了些,他清了清嗓,“先吃饭吧,菜一会凉了。”
经过此节,衆人这顿饭吃的都有些心不在焉,都知道孟怜笙跟三晋督理勾搭上了,谁知道他能把人迷成这样。
三晋时报的大小一张能写下四百字,这篇戏评却足足写了十篇有馀,就算是情话也不能一句不带重复的说了四千多字然後公之于衆吧?而且不是说良帅没读过什麽书吗?这雇人写的吧?
吃过饭後,又是几场戏,孟怜笙与陈问柳唱由李思远编词的《南柯记》时状态不如之前亢奋,是他一贯稳健的台风。
接连着是莫凌的《坐楼杀惜》,莫凌虽不是如孟怜笙这般的大角儿,但因其师门密宗奇绝的步法斩获了许多戏迷。
他们唱戏的在这世道没点关系是唱不出头的,他相貌又是典型的男人女相,这几年身边都不缺好这口的达官贵人捧他。
上弦月高挂梧桐枝上,这次梨园联谊到了尾声,轮到孟怜笙讲话,他在瞩目里上台,对着电喇叭说:
“自徽班进京的百年里,京剧不断发扬,梨园子弟开枝散叶,到了如今梅竹修出国演出让这门艺术走出国门,京剧不再只是为人呷玩取乐的玩意儿了,可最近我总能看到新闻小报上说要想京剧发展,就要先西化。”
“我对此并不全部赞同,为何因为洋人看京剧,我们就要学习西方的话剧,此种说法实在崇洋媚外,京剧想发展,最先要做的是传承与认同,这并不是固步自封,创新的前提是要继承传统,先领悟,再传承,最後是创新。”
……
他避开梨园行的风气只谈对这门艺术的理解说了一气,最後孟怜笙挺拔如竹,语气郑重:“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愿京剧艺术锦绣常青,我宣布,此次梨园联谊会圆满结束。”
“慢着!”
①:出自《新竹》郑板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