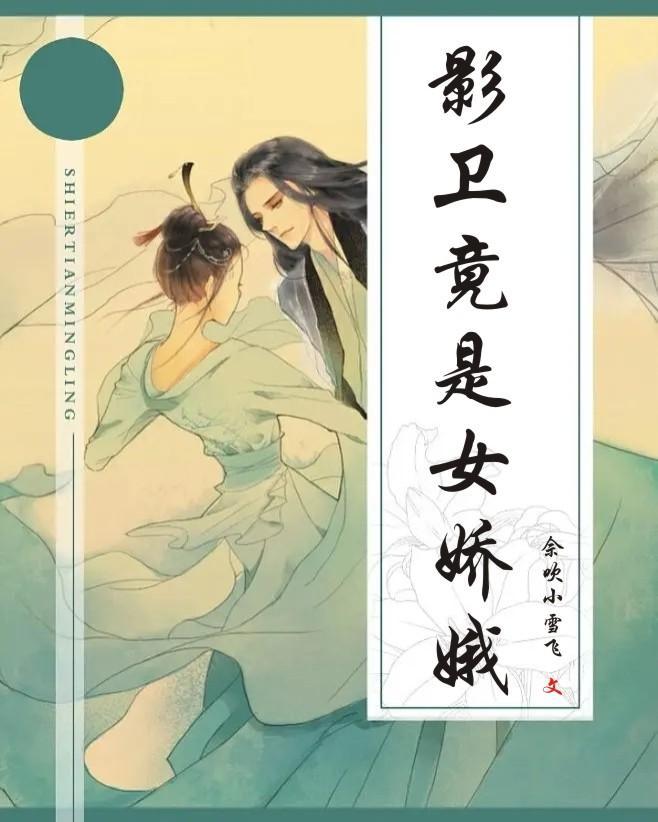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斯文下一句是什么 > 第30章 又绿江南 花常好月长明(第3页)
第30章 又绿江南 花常好月长明(第3页)
灯下的男人神色倦懒清泊,楚楚衣冠上那一点皱褶仿佛只是坐太久压出来的纹理。
除了那两片和她一样鲜红的唇还无法抵赖,刚才禁锢着她缠绵好似皆是幻影。
他直白地告诉她:“你要去凑热闹的那个场子,在隔壁。”
他坐远了些,仿佛也将沈妍刚刚被锁住的四肢给卸下枷锁了似的。
沈妍也顾不上他话里话外看不上的语气字眼,自己闭了闭眼,做了个深呼吸,二话没说起身要走。
秦鹤将她按下,幽幽地说了句:“已经散了。”
他颇为无奈盯着她,像是菩萨在怜惜怎麽也点不透的弟子,长长叹息了一声。
“你忘了我什麽都能给?”
这下她总算听明白了。
他不许她去找别人,是为了让她只能来找他。
沈妍注视着他慢慢擡起手臂,温凉指尖去触碰她红肿的唇瓣。起初是轻轻地点,而後越发下狠手,施虐似的往下压。
他像在用疼痛刺激她的神经,逼她去记起什麽。
沈妍的眼窝里霎时蓄清凌凌的泪。
直到刚刚,她一直像个被牵着魂的木偶,轻而易举回到了许多年前,任由他打点拿捏。
她只用听话。
间或暗暗去揣猜他对自己有几分真心。
但这句问出来,反而将她摇醒。
沈妍一挥手将他挡开,轻声:“忘了。”
“该忘了。”
他眼眸一冷,薄唇刚要啓声,被她骤然堵上。
沈妍环上他的後颈,贴着他,却不吻他,身骨软绵绵地化在他掌心。
“秦鹤,连你都终于意识到我长大了,不是麽。”
她话音轻巧平静,外衫彻底滑落,凹凸有致的身材裹在旗袍里,像是在提醒他。
“再也不是被你护在羽翼下什麽都不用管的小孩儿了。”
她肆无忌惮地陷在他怀里,给他设了个乍看起来两相无解的棋局。
秦鹤的手腕垂在膝上,久久没伸手去揽她。
可最後,他却单手撑着头看她,掌心覆了覆她白腻瓷胚似的脸颊,唇边渐渐泛起松惬的笑,“嗯,也行。”
他那时的神情过于淡静,一丝波澜都没有,以至于沈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为,是自己设的两难题面困住了他。
纵使秦鹤喝醉了,也不会一面与她辗转厮磨,一面又拿她当个手无寸铁的孩子那样护着。
但还有另一个答案,轻而易举就能破局。
那是她压根没想过的可能。
沈妍从临河三楼走下来时,一茬新客已经换进来,台上仍是那两位演员,唱的还是《赏中秋》。
花常好,月长明。
可她却不知怎的想起後面《断桥》的唱词。
“已经是,好花偏遇无情雨,明月偏逢万里云。”